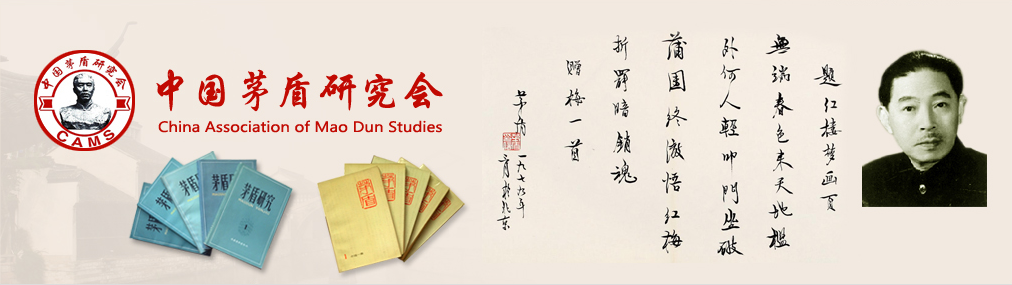空前的盛会 良好的开端——全国首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述评
崧巍
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首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历时八天,罗荪同志主持并致开幕词,周扬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老一辈作家、学者张光年、沙汀、冯牧、陈荒煤、周而复、黄源、臧克家、吴组缃、姚雪垠、戈宝权、孙席珍、王瑶、唐弢、田仲济、林焕平等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开得热烈而隆重,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一百多篇论文,并在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茅盾研究学会。
代表们回顾茅盾研究的历史,几十年来,党对茅盾有两次重要评价: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转折时期的党的“七大”之后,在重庆文化界举行的茅盾诞辰五十周年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庆祝会上,王若飞同志代表党中央对茅盾所作的评价;另一次是在茅盾追悼大会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的悼词。在讲话和悼词中,党中央充分肯定了茅盾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茅盾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作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这次学术讨论会,正是在党中央对茅盾所作的历史性评价的总精神指导下,第一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就茅盾的生平思想、多方面的文学成就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这次学术讨论会,有四个突出的特点。第一,许多论文涉及了过去的一些被忽视的问题,诸如茅盾的美学思想,茅盾的短篇小说创作,茅盾的散文、杂文、政论以及文学翻译等,扩大了研究领域。第二,资料方面,也有新的发掘与发现。第三,在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上,注意实事求是,注意研究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第四,茅盾研究工作者老中青三代同堂,共同切磋。老一代继续精进,中年研究者提出更有分量的论文,一批二、三十岁的青年研究者思想敏捷,观点新颖,使人感到茅盾研究工作后继有人。
以上四个特点,也是大会开得好、开得成功、今后可以对茅盾研究的前景持乐观态度的重要标志和根据。
由于茅盾研究的历史为时不长,这支研究队伍尚较年轻,所以发言和论文中也不无偏颇。这是前进过程中难免的现象,其中有的在会上也有所纠正。另外一些问题,则存在着分歧。这当然是正常现象。代表们本着百家争鸣方针互相切磋琢磨。使有争论的问题的探讨有较大的进展。讨论气氛也十分融洽,表现了良好的学风与会风。
讨论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是关于茅盾的思想发展、特别是早期文艺思想发展,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集中在茅盾什么时候形成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上。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茅盾世界观转变是过渡期很长,曲折较多,直到进入三十年代,才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持这种观点的同志重要的根据是一九二七年茅盾脱离了党组织,思想上消沉、幻灭。表现了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绪(茅盾自己也承认),直到一九二九年写《创造》与《虹》时,才体现了他的思想复苏,以一九三O年回国参加左联为标志,才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作家。许多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一个作家的世界观的转变,要看其根本立场。而不能要求其完成质变后,思想就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纯,而不允许有起伏,有摇摆。如果这么要求,真正合乎“标准”的无产阶级作家就没有几个,因为人的世界观是复杂的,其内部大都存在着对立面。关键看什么思想占主导方面。只要其主导方面是无产阶级的,就可以认为其世界观发生了质变。因此,以茅盾一九二七年的摇摆为据否认其此前已发生了世界观的质变,是不妥的;以一九二七年的摇摆为据否认其此前已发生了世界观的质变,是不妥的;以一九二七年失去组织联系为据更是站不住脚的。党中央在茅盾逝世时作出的复茅盾的党籍,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的决定充分证明了这个问题。
但在究竟什么时间发生了质变的问题上,持后一观点的同志中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茅盾大体上是一九二五年完成了世界观的的质变。其重要标志是《论无产阶级艺术》、《造成有志研究文学者》、《文学者的新使命》、《现成的希望》等四篇文章的发表。这批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无产阶级文艺形成的历史过程、文艺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艺产生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文艺的内容与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它的社会作用以及人民对无产阶级作家的要求,等等。这一切标志着茅盾对其阶级观点比较模糊的“为人生”的文艺观的扬弃和无产阶级的文艺观的确立。这是他早期文艺观和世界观的一个飞跃。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为人生的文艺观的理论基础是进化唯物论,它在认识论、历史观上虽然基本上是唯物的,且也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反映了他在社会观上受明显的人性论的影响。缺乏明确的无产阶级观点。虽然不同于欧洲的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但基本上属于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范畴。而茅盾一九二五年确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文艺观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论。除能较全面地谙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外,还明确地把无产阶级阶级观点引入了对社会历史与文艺问题的研究分析,明显地属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范畴,体现了其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
有的同志赞成这些分析,但不赞成以一九二五年为茅盾世界观发生质变的分水岭,认为最迟从一九二二年起,茅盾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质变。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茅盾说过:“进化论,当然我研究过,对我有影响,不过那时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新青年》。”而《新青年》在十月革命刚发生即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茅盾自己也说在建党前夕就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学习小组。建党之后,他作第一批共产党员在一九二一年地下党的刊物《共产党》第三号上发表的《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等论文,就指出中国的前途是“立即举行无产阶级革命”,“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都归为生产劳工所有,一切权力都归劳工们执掌,直到尽灭一分一毫的掠夺制度,资本主义决不能复活为止”。体现了此前他译介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文献(包括《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等一批文章)的基本观点和立场。说明他建党前后即已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阶级斗争实际问题。一九二二年发表的《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是其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文艺问题的标志。至于这前后茅盾用“为人生”、“平民”、“自然主义”等词,那是“借用”。因为当时茅盾是“介绍学术”,是“借钟馗打鬼”。但钟馗是钟馗,借者自是借者。不能因此而判定茅盾世界观的质的规定性。何况他在一九二四年就号召“不同派别的文学者联合起来……一致鼓吹无产阶级为自己而战”(《欧占十年纪念》,1924年8月《文学周报》第136、137期),这也早于一九二五年。
这种观点因为有一系列新材料和新发现的茅盾佚文作依据,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但也有同志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加入共产党或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的标志不仅要看其理论的政治的信仰,还要看其社会实践的种种情况的性质。于是,大家在衡量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与立场的标准上也展开了不同意思的争论。争论的结果趋向一致:基本的标志是全面看其理论与实践的性质及二者是否一致和统一。
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茅盾与现代文学思潮的关系。这也关系到茅盾早期文艺思想的发展问题。不少代表坚持传统看法,认为茅盾是经过自然主义进而倡导现实主义,并逐步发展为革命现实主义的。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各种意见相互交叉,思想比较活跃,分歧点也比较复杂。
首先对茅盾倡导自然主义的看法与估价就不尽一致,一种看法认为茅盾倡导的自然主义尽管有现实主义的合理内核,但仍然是以西方自然主义思潮为蓝本的,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也比较明显。他的早期创作,特别是《蚀》和早期某些短篇中都留有自然主义的痕迹。这种印痕甚至在代表作《子夜》中也偶有所见。另一种看法与上述观点相左,认为茅盾介绍与倡导的自然主义其基本内容是现实主义。与左拉的自然主义固然不同,与龚古尔兄弟也不相同。并且不赞成把茅盾倡导自然主义看得过重。认为这是他广泛介绍世界种种现代文艺思潮的一部分,只是他为反对鸳鸯蝴蝶派与黑幕小说以及文以载道的种种封建文学而采取的重要步骤,也属于借钟馗以打鬼的性质。茅盾所看重的是自然主义关于实地观察与客观描写的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实质上已不同于西欧的自然主义。例如他曾提出若以“荦荦大端”的“共通精神以为标准”,“法国的福楼拜、左拉等人和德国的霍普特曼,西班牙的柴玛萨斯,意大利的塞拉哇,俄国的契诃夫,英国的华滋华斯,美国的德莱塞等人,究竟还是可以拉在一起的。请他们同住在‘自然主义’——或者称它是写实主义也可以,但只能有一,不能同时有二——的大厅里,我想他们未必竟不高兴吧”。茅盾有时还把巴尔扎克也称作自然主义大师。可见他倡导的自然主义其精神实质是指现实主义。有些代表还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没有能分得清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这种历史真寮现象在早期现代文学史上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也承认茅盾的确也赞成自然主义,其早期创作中也有自然主义的痕迹。另外的同志则认为不必讳言茅盾倡导的就是自然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自然主义具有两重性,它有局限,也有进步意义,它和现实主义有共同点,认为自然主义具有两重性,它有局限,也有进步意义,它和现实主义有共同点,表现在“它们对创作方法和世界观之间关系的认识的一致性——创作方法上的真实性使它们能够克服世界观上的偏见”。借此可弥补世界观的不足。作家的同情与倾向是“自然而然地渗入艺术画面之中,而不是作者主观意念的强加”。这是导致茅盾把二者混淆了的原因。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客观描写不是机械的照相”,“只要描写得当,同样可以反映出生活的本质”。他不同意茅盾本人和有的论者所说茅盾早期创作并未按照左接方式,他认为茅盾早期的创作“是想按照自然主义创作的,但他和左拉一样,也是不成功的”。他认为自然主义的“真实性与客观描写有纠正封建文学的革命的进步的作用。茅盾因此建立了历史功绩”。至于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淆“是文艺思想在历史上的混乱,其责任并不能归咎于年轻的茅盾”。既然当时大家都没弄清楚,我们今天更不应苛责于前人。
但大家一致认为,不管怎么评价茅盾与其倡导的自然主义,都应肯定茅盾除了自然主义的生物性描写等等内容,而是吸取了其合理的内核。这个认识是统一的。
有几篇论文作者提出茅盾倡导自然主义只是一个过渡,不是其终极目的。其终极目的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新浪漫主义。他们认为茅盾从文艺进化论观点出发,认为“西洋小说已由浪漫主义进而为写实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我国却还停留在写实以前”,因而认为“要介绍新派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介绍起”。但“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他们援引五十年代茅盾的《夜读偶记》中对新浪漫主义作的这样的解释:“现在我们总称为‘现代派’的半打多的‘主义’,就是这个东西”,但它的“现代派”的“逃避现实”,歪曲现实,亦即反现实“稍稍有点区别”。因为“当时使用‘新浪漫主义’这个术语的人们把初期象征派和罗曼·罗兰的早期作品都作为‘新浪漫主义’一律看待的”。有的代表认为提倡新浪漫主义是和茅盾的“为人生”的文艺主张相一致的。茅盾所倡导的新浪漫主义就是罗曼·罗兰的新理想主义,目的是为了克服写实主义重客观,轻主观的偏颇,是为了发扬革命的解放的创新的“浪漫的精神”,取其“兼观察与想象”的优点以求“综合地表现人生”。他们认为这是基本上符合时代对新文学提出的历史要求的。但当时茅盾尚未能认识新浪漫主义内涵的复杂性,也过高评价了罗曼·罗兰的新理想主义。
相当一部分同志不赞成这种估计。认为茅盾在“五四”前后所介绍的各种现代文艺思潮与流派,并非他一一赞成的。即便他当时一度赞成,也并非他一贯赞成。这只是他广泛介绍、择善而从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今天不能根据个别论文、个别时间就下总的结论。从茅盾的文艺主张和文艺创作总的发展善和总的趋势来看,他是沿着自然主义——写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基本轨道稳步前进的。作为现实主义的主要倡导人,茅盾早期的文学主张是现实主义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师,他的创作也是现实主义的。从总的倾向看,自然主义也好,新浪漫主义也好,只是茅盾文艺思想的局部,和其总倾向并无多大关系,对他的创作的影响也是不大的。
讨论的第三个焦点问题是茅盾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特征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茅盾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特征是提倡文艺的时代性。它贯串着茅盾一生的文学活动,随着他的文学思想的根本衍变,使得他对时代文学主张的阐释也有了质变。有些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反对的角度却不相同。一种意见认为茅盾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尽管也包含着时代性的内容,但却不是其唯一特征。而是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时代性决非茅盾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独特内容,而为许多进步的理论家作家所共有。如鲁迅的现实主义理论就很强调时代性内容。与茅盾同期倡导积极浪漫主义的郭沫若,其文艺思想也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在郭沫若的理论与创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茅盾也好,郭沫若也好,其早期文艺思想都体现着鲜明的“五四”时代精神。从世界范围看也是如此,无论是拜伦、雨果的浪漫主义还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其文艺思想内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内容。可见,时代性问题在更大范围反映着文艺与现实、文艺与时代之关系的普遍性,而不是某个作家或理论家的文艺主张的独特性。还有的同志在文章中把茅盾的现实主义概括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上看,茅盾强调凭借文学反映时代与人生的真实性,而且他的文学真实观的严峻性,最终仍要归结到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目的上去。第二,茅盾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中具有清醒的理性做强的特征。在理性、情感、形象之间,理性隐藏得最深,职能却最为重要。它决定形象的思想内涵的深度、厚度,也是情感的严格控制者。他很重视文学的情感作用,也不主张破坏“心灵的强烈冲动”而导致概念化。他的现实主义的理性化是对丰厚的生活经验“研究”“推敲”之后的结果,是理性渗入情感的产物。是作家在正确世界观指导下取得的对生活的清醒透辟的认识而化为自己的“天性”与“本能”之后的表现形态。第三,茅盾的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文艺思想体系,强调现实主义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也注意融汇其他流派与创作方法的某些技巧,因此,茅盾恪守现实主义的本质精神而又广为吸收;坚持原则却并非自我封闭,大胆开放却并不随意调和。他走着自己独立的现实主义途径。
在茅盾作品研究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对《子夜》及其主人公吴荪甫的认识就不一致。一种意见坚持吴荪甫是反动的资本家的观点,认为这项“反动的”帽子决不能摘;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认为吴荪甫是具有法兰西性格的反帝,反封建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英雄人物。多数同志则认为:吴荪甫是在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投靠并追随买办资产阶级之后的一九三O年的特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真实地反映着他那特定时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因此不应该把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性格作简单的阶级定性;而应具体剖析其复杂内容,充分认识其性格的丰满性。例如他既具有那一时代投靠买办阶级后的民族资产阶级反动的一面,又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买办资本主义的爱国主义,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进步要求与强烈欲望。因此,他有可能回到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中来。茅盾的艺术描写的深刻性恰恰在此,吴荪甫典型性格的现实意义也恰恰在此。
对茅盾创作的评价中存在另一个分歧是茅盾的小说是不是“主题先行”。大家都认为,茅盾的创作和“四人帮”所搞的那种“主题先行论”是有质的区别的,完全不是一码事。但在排除了上述问题的前提下,怎么看这个现象方面,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评论任何事情都要放在当时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来评论,那个时候茅盾的“主题先行”——假设是这样的话——同后来的“主题先行”完全不一样。那时的作家一般还不具备“深入工农兵”的条件。在当时条件下的“主题先行”就带动了作家学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分析社会现象。这样的“主题先行”是具有开创性的,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把作家带到革命现实主义上去了。使年轻作者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大多数同志认为,即便对“主题先行”作了这样的诠释,也还不宜用来说明茅盾的创作。发言中对此作了多方面的解释,举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主题先行”是“四人帮”时期用政治概念、反动的创作意图去图解生活的一种做法,它不同于中国古文论中所主张的“意在笔先”。所谓“意在笔先”包括了创作之前具备的明确的目的性,也包括创作具有明确的写作意图。只要这种立意是来源于生活实践,那么它就属于原始素材积累阶段的认识生活的过程。是主题思想提炼过程的必经阶段。不能叫做“主题先行”。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主题”也不应该“后行”。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是有意图的,毫无意图,信笔所之,是不符合创作规律的。茅盾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他的创作思想是从“为人生”发展为“为无产阶级”的。他的创作实践证明他总的说是从生活出发的,他本人一向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更不赞成“主题先行”。除了《三人行》等极个别的作品,他的作品也不是概念化的。第二,茅盾的创作大都是先有人物,后形成主题。包括《字夜》中的吴荪甫,也有真人为模特儿。茅盾对这些原型的了解认识先于他的创作意图,更先于他的《子夜》的主题思想的形成。他特别强调研究人和人物关系。他一向主张“人”是他首先观照的中心,他是首先从人物和人与人的关系出发的,而不是首先从主题出发的。第三,从创作过程中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的观点看,茅盾倒并不排斥逻辑思维对文艺创作的作用。他一向认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的正确。而社会对于我们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会现象的正确而有为的反映!”但这并没超过认识生活与再现生活的基本规律,关键在于茅盾是从生活出发、并且以生活的形象作艺术的再现。这就不能说“主题先行”。反之,创作排斥逻辑思维是不成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排除逻辑思维单靠形象思维就能把创作过程很好地完成。第四,也不能把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叫做“主题先行”。茅盾所说“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指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其创作的作家。茅盾自己的创作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先进世界观指导下创作出来的。这使他的认识生活、积累素材、典型提炼、艺术构思取得了更高的立足点,使其作品加强了社会性、时代性和史诗性,总之大多数人不倾向于用“主题先行”的观念分析茅盾的作品。
这次学术讨论会尽管存在着许多争论,但整个气氛十分融洽。大家平心静气地各抒己见。本着切磋琢磨、相互学习的态度追求真理。不同观点的争论非常认真,但绝无强加于人或扣大帽子的事情发生。这反映了近年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百家争鸣的风气已取代了“左”倾思潮泛滥时期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恶劣学风。
这次讨论还有一个特点:许多文章和发言都批评了“左”倾观点和“右”倾思潮的流毒。都注意拨乱反正。这一点最集中地映在对茅盾的文学业绩和他的历史功绩的再认识、再评价上。大家一致认为过去对茅盾及其作品的评价过低。从二十年代末期以来,“左”倾思潮的几起几落都对茅盾研究有所冲击。今天应该重新认识,重新评价了。
与会的代表有一种历史性的感觉:茅盾研究的新局面、是党中央自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深入人心的一种表现。大家相信,茅盾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新阶段,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