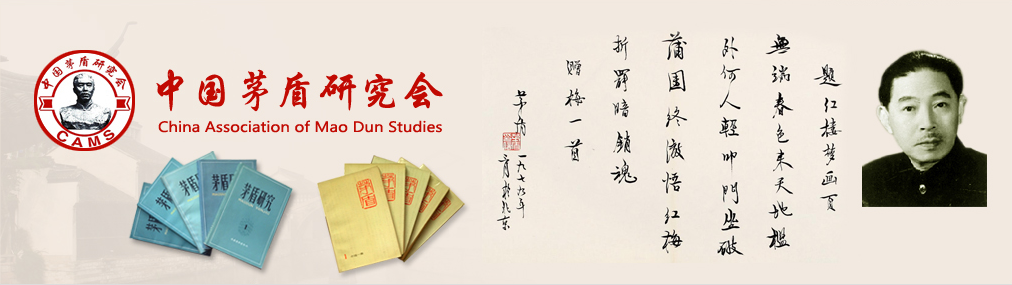有所进展 有所提高——全国第二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述评
张颂南
全国第二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至十二日在杭州西湖宾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报社,出版社,社会科学院的茅盾研究工作者一百多人,提交讨论会论文九十多篇。黄源、陈学昭、韦韬等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讨论会,历时七天,以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为主,其间还组织与会者去浙江桐乡乌镇,瞻仰了修饰一新的茅盾故居。
提交这次讨论会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比较集中的是茅盾的文艺理论(包括文艺思想、文艺批评、文学思潮、美学思想等)和小说创作。也有过去研究较少如历史小说、童话、杂文、报告文学、翻译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在研究方法方面,综合系统的研究,宏观的研究,比较的研究都比上届讨论会有所加强。会议汇报了研究论文的新进展和介绍了国外茅盾研究的新情况,在提交论文的基础上,就茅盾的文艺思想体系和创作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认识和估价。现将这次讨论会的论文要点和讨论情况概括的述评如下:
一、关于茅盾的文艺理论
1、茅盾早期的文艺理论贡献
茅盾的革命文学活动是从理论研究、外国文艺思潮评介以及对创作的评论开始的。鲁迅以小说、郭沫若以诗歌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早期的茅盾则以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为保证新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同志说:“五四是特别需要理论的时代,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一次有意识组织的文学运动,它使我国文学在从来没有过的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出现了理论指导创作,创作自觉接受理论指导的新局面”。这个新局面的开创,固然在五四文学革命时,就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驱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和旧文学的文学主张,而最为自觉、最为辛勤,也最为持久地耕耘在新文学理论园地里的是茅盾(即沈雁冰)。他当时出于反帝反封建的需要,为了彻底改造旧的封建主义的文学观,致力于对西方近代文学思潮的研究与介绍,尽管这种介绍还存在着“包罗万象”和有些提法显得概念混淆的缺点,但“他援用西方近代文学理论搭起的一个理论框架,以它的整体化,科学性现实性,彻底改变了我国古代文论的格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学理论和整个文学事业的‘现代化’进程。”
不少论文也从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长河中论述了茅盾的理论贡献。有的同志作了一个统计,茅盾从1919年到1980年,写下的文艺评论,总计约四百五十万字,作过较全面评价的现代作家有鲁迅、郭沫若、叶圣陶、丁玲、沙汀、臧克家、陆文夫、玛拉沁夫等三十多人,重点评论过的作品,有《阿Q正传》、《女神》、《倪焕之》、《北京人》、《暴风骤雨》、《白毛女》、《李家庄的变迁》、《青春之歌》、《李自成》等九十多部。因而认为茅盾的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时间之长,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堪称是中国的别林斯基,有的论文也认为茅盾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独创和贡献,就现代文学的总的影响来说,除了鲁迅,茅盾是第二人,就现代文学批评的贡献来说,则茅盾居于首位。
2、茅盾文艺思想的特征
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时,有的同志提出茅盾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特征是提倡文艺的时代性。但当时更多的是集中在“时代性”究竟是不是茅盾文艺思想的特征的讨论上,而对“时代性”的概念,特别是茅盾提出的文艺要求表现“时代性”的特殊涵义还缺乏深入的探讨。在这次提交的论文中,对茅盾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特征问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开拓。与第一次讨论会相比的不同特点,是着重于探讨究竟什么是茅盾倡导的“时代性”?这就使问题深入了一步。
很多论文引用了茅盾在《读〈倪焕之〉》中的一段话,这短话是:
所谓时代性,我认为,在表现了时代的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动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换言之,既是怎样促进历史进入了必然的新时代,再换一句话说,既是怎样由于人们的集团的活动而及早实现了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意义下,方是时代的新现实派文学所要表现的时代性。
茅盾这段话是在和创造社太阳社进行理论论争时说的,这从一方面看,它是对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文艺作品的时代性的片面认识的一种批评,即反对席勒式的单纯代号筒的倾向,而就茅盾自己来说,乃是一个发展了的新的认识。一九二二年茅盾写的《文学与人生》在论述时代或时代精神时,不难看出他还受泰纳的艺术哲学的影响,他把时代与文学,时代与艺术仅仅看作是一种“形与影”的关系。而在这段话里,则阐明了时代不但给人们以怎样的影响,而且人们的活动又反过来怎样积极影响推动时代的前进,这才是文艺所要表现的时代性。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对无产阶级既敢于正视现实又有信心改造客观世界的充分肯定。当然也包括着对人的社会价值的充分肯定。
有的论文,在思考茅盾提出的“时代性”时,还把与茅盾的创作个性联系起来研究,提出“茅盾的创作以明确的目的性,强烈的社会性与时代性,以广阔宏伟的气势与规模卓立于我国现代文坛,其鲜明的创作个性首先是体现在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提炼上”,“从周围的人生中抉取伟大时代意义的题材,写时代的大题材”这是茅盾选择题材的最基本的特点。文章还指出茅盾在描写时代的大题材中,又特别注意社会经济的题材,描写与政治密切联系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就是茅盾所说的“社会经济结构”。他的创作往往从政治的角度揭示旧中国经济破产的前因后果,从政治的眼光看经济,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这种特殊的视角,显示出了茅盾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独特思想风貌。也有的论文提到,茅盾揭示新文学运动中各种思想流派的纷陈消长,也是从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我国政治斗争的迅速变化中去寻求答案,说明它们的根本原因的。
提出这一问题,对理解茅盾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是很有启发的,这要比一般的谈茅盾创作的整体化,时代性有更深刻的内容。茅盾不只一次的告诫文艺工作者,要研究社会科学,特别要阅读“指导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书籍”,这是一份十分值得珍惜的思想遗产,因为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道德感情的变化,人们的心理、性格的变化,所觉察,也往往缺乏批评的勇气,因为公式化概念化这种创作倾向,一般说是“左”的思想的产物,它具有热剌剌的“革命”气味,所有批评这种倾向尤须有胆识和勇气。茅盾不愧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杰出的理论家,对于各个时期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他都勇于以尖锐的批评,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的崇高革命责任感与维护现实主义创作的严肃认真精神。
4、茅盾美学思想的特点
有的论文认为:茅盾在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姿态步入中国现代文坛开始,就毕生不懈地致力于对文学进行求真和具备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标准的理论思考与探索。并逐步地形成了一个富有他个人特色的美学思想体系。这个美的思想体系最重大的特点,是在吸收西方美学精华的同时,又融合了东方美学的传统,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作出了贡献。比如他一方面要求文学作品能再现客观现实的真实,另一方也要文学作品能表现其内在的精神,要讲究“美”,讲究“意境”,讲究“神韵”。要有“韵外之歌”,“味外之旨”,“气韵生动”。他认为文学作品“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差异而保留了‘神韵’,因为文学的功能在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富于‘神韵’的多而在‘形貌’的少”。看来,茅盾是主张文艺作品应该是形神兼备的,而在“形”与“神”这两者中,他又特别强调“神”,在这一点上,是与我国民族的美学传统相一致的。茅盾对美的理解是比较内在的,不仅仅是形式的,所以他也非常注意文学的感情因素和文学艺术的表情功能。他认为文学作品要能够使人们得到“热烈的情结的颤动”,要能够使人们“感激而下泪”。这和我国传统美学中“发愤而抒情”“诗为心声”的论证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旧俄时代的果戈理因为怀着他们固有的“高贵的愤怒”抨击了沙皇俄国农奴制统治的社会,而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但因为他没有能够提高到先进的政治观点上来,而出现了“诗人和思想家在他身上发生冲突”的弱点。而矛盾的理论和创作,正是在这种中西结合的美学思想指导下,而达到了“诗人和思想家在他身上的统一”。
也有的同志指出,矛盾要求真、善、美一致的美学思想表现在文学主张和文学批评上,是对“假”文学的批判和对“真”文学的倡导是对“艺术至上”的批判和对“为人生”的艺术的提倡,是对标语口号文学的批判和对艺术特点的重视。表现在他的创作上,则是既从广阔的社会生活、社会斗争中,从时代的主潮中去发现美,挖掘美,又多方面地吸收借鉴中外艺术经验,熔铸冶炼为自己作品的血肉,形成一种浩瀚雄伟的“力之美”。
二、茅盾的小说创作
1.茅盾小说创作的理性思维
有的论文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无疑是一个独标高格的作家,他的作品明显呈现出带有理性化特点的社会分析色彩,通过文学的命题提出了重大的社会科学命题。这种带有茅盾式‘纹章印记’的创作特色,很少为同时代作家所具有,在中国现实小说的现实主义流派中带有开创性的。”关于这一问题,也有同志提出理性色彩对艺术品来说究竟其得失如何的问题。不少同志认为:文艺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茅盾对“艺术直觉”是相当冷淡的,理性思考正是他小说创作的个性,不应违避这一点,这不是他的缺点,正是他的优点。有的同志还指出:“茅盾应用社会分析,理性分析于创作实践,是同尊重艺术本身的规律结合起来的,是使思想赋予艺术的生命才使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他的卓越经验:一是“哲学家和观察家”的结合,二是研究社会侧重在对人的研究,三是艺术的构思中两种思维的结合。
2、茅盾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
在探讨茅盾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特色中,有的论文总计了茅盾反映生活和再现生活的两种基本方式,即托尔斯泰的方式和左拉的方式,左拉的方式是“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托尔斯泰的方式是“经验了人生之后才来做小说”。茅盾的小说装作就是这两种方式的交替使用或相互结合的产物。对茅盾小说写法上的创新论文则作了这样的概括:认为早期,茅盾用的是一种“内向发展”的写法,即西欧小说常用的以一两个人物的性格刻划为中心着重雕镂人物性格特别是其内心世界,内心感受的写法。三十年代是“外向发展”的写法,即把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西欧小说笔法和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的写法结合起来,到三十年代后半和四十年代,是把“内向发展”和“外向发展”两种笔法结合起来,有时二者结合以“内向发展”为主的写法。
有的论文还从茅盾的文体风格方面论述了茅盾的创作特点,认为茅盾对于现代文学文体的最主要的贡献,是开创了“史诗”式的小说文体,他宣告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结构体制上的革命,这就是以情节为主的“戏剧”方法,改革为一种以性格为主的“思想分析”的方法,这较之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就扩大了容量和密度。
3、茅盾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因素
这次讨论会中,有两篇关于茅盾小说的象征手法和象征主义的探索的论文,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和注意。茅盾散文中的象征色彩已早被研究者所注意,而比较系统集中的论述茅盾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因素,这两篇论文还是首列。论文认为,在茅盾的小说创作中,《追求》是一部以“外界的物质的动静”为描写对象,来表现作家主观思想情绪起伏变化的象征主义小说。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作家苦闷“灵魂”的跃动和呼喊,都是作家为表现苦闷情绪而建立的“方程式”。认为《追求》中的“青年的不满于现状,苦闷,求出路”,虽然是客观的真实,但对于作家的创作意图来说,他们统统是一种象征,是茅盾在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的“苦闷的象征”。论文还指出“我们不能被茅盾‘客观的真实’描写所迷惑,误认《追求》是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小说,而忽视了茅盾在借鉴象征主义的艺术方法时对象征体的独特处置。”
三、不同的看法和分歧的意见
主要表现在关于茅盾革命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上,接触到了以下几个相关的问题:
1、一对茅盾早期倡导的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不同看法。
2、二是对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创作的《蚀》和论文《从牯岭到东京》的不同评价。
3、三是一九二五年茅盾能不能说是一个革命现实主义者的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即倡导自然主义的问题,有的论文认为二十年代初,茅盾使用“自然主义”这一提法,从实质上、总体上看,他是反自然主义赞成现实主义的。这只是概念上理论上的一点混乱,把自然主义说成了现实主义,具体的说,就是把自然主义的照实当成了现实主义的真实。并以此来反对当时脱离实际的“向壁虚造”的颓风。
但有的论文认为“茅盾介绍和提倡自然主义是为了纠正新文坛向壁虚造,主观杜撰的不良创作倾向,这是事实。但又不是事实的全部,——的确部分的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五四时期茅盾的文艺观是复杂而矛盾的,不能笼统地归结为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只是包含相当的现实主义成分”。
关于茅盾倡导的新浪漫主义,有的同志认为,茅盾主张提倡新浪漫主义,包括着他自己的对中国社会、时代的新的创作方法的探索,好像马克思早期使用“异化”的概念一样,他在介绍中有许多具体看法,主要是把客观描写与主观表现结合起来。有的同志指出:新浪漫主义是一种运动,这种潮流既不是一次性整体的来到中国,就接受者来说,也必然经过从个别接触到全面了解,从朦胧认识到本质把握的过程,因此,不能只以作家自己在回忆录中的提示为满足,要考虑其历史筛选和积淀的因素,应在各种思潮纷纭杂陈的时代背景下结合茅盾的思想变化,来理解他倡导新浪漫主义的历史的实际的内容。
对第二个问题,有的论文认为大革命失败,到一九二九年间,是茅盾文艺思想变化波动较大的阶段,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倒退”或“停滞”,其主要标志是一九二八年写的《蚀》和一九二五年写的《论无产阶级艺术》的观点不一致。
有的论文则认为茅盾的《蚀》表现了作家勇于正视现实反映现实的坦率精神,是“在真善美三者的关系上比较准确地达到了统一和融合”的作品,而在《蚀》以后,由于作家创作思想的转换,反给他的部分作品带来了令人惋惜的损失,即抽象的思维和概念所造成的部分的对“美”与“真”的忽视。显然,这种意见与前一种看法有些针锋相对。
由于对以上两个问题看法不一致,因此对一九二五年茅盾能不能说是一个革命现实主义者的看法也就不同,认为还不能说是一个革命现实主义者的理由是:一九二五年提出的理论,毕竟限于别国的经验和书本认识,它还未能和中国的社会和文学完全结合起来,特别是个人尚缺乏创作实践,因此一九二七年产生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世界观上的矛盾。
另一种说法,认为“作为一个理论家兼创作家,可以全面考察,但不能要求两者都达到一致为标准,不然就有些苛求了。理论与创作是有距离的,主要应该看他的理论体系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说二五年一年太机械,跨得时间太长也不好,这应以模糊数学的办法解决,可以说是二十年代中期完成了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转度,《论无产阶级艺术》作为主要标注,当然质变后还有量变。”
此外,对茅盾小说创作中的象征主义因素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茅盾只是运用了一些象征方法,要把一般的象征与象征主义加以区别。从茅盾的创作来看,象征的整体性谈不上,只有艺术手法的象征。
四、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新收获
除论文外,提交讨论会的还有若干篇关于茅盾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的文章,如钱诚一同志的《关于茅盾开始创作的年份和处女作的疑问》,考证了《小说月刊》第十二卷第一号上署名“慕之”题为《不幸的人》的一篇作品,认为这是茅盾写的第一篇小说,从而对学术界历来认为《幻灭》是茅盾的处女作的论断提出了异议。翟同泰同志的《茅盾早期社会和革命活动拾遗》,对茅盾《桐乡青年社》活动的补充,对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茅盾担任过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长的调查和考证,以及茅盾在上海大学任课时间和授课内容的订正落实,还有黄川同志整理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关系大事记》,刘光宇同志整理的《茅盾几年研究鲁迅记略》,这些都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茅盾的思想和创作提供了可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