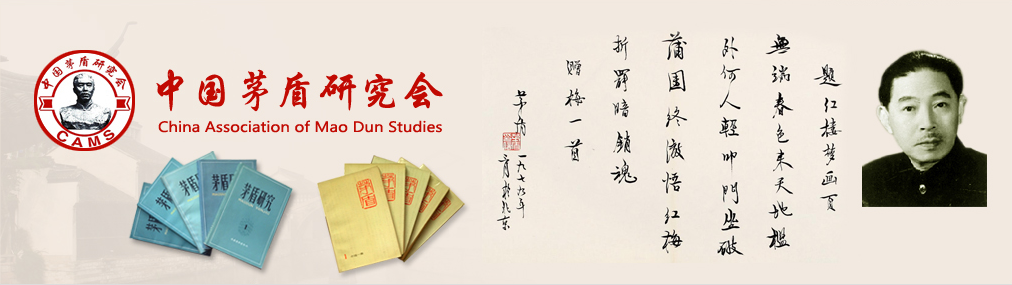误读现象与茅盾研究
孙中田
一
误读是与正解相对应的。但在文学历史的过程中,何者是误读,何者是正解,它们的正负价值,有时很难黑白分明,所以在历史的天平上,价值取向,常常呈现出错位、偏离的浮沉状态。这与文本的意蕴有关,与时代、文化风尚的变异、作家的意向以及读者审美探求的目光都有关系。正是如此,这些作品在当代获得良好影响并得意传播,但时过境迁,审美情趣转化,他的位置和影响也因之而有浮沉,这是常有的事。据唐人解读史考察,杜甫的位置就颇有些变异。《何岳英林集》选入诗人24位。其中常见录15首;李白录13首;王维录15首;王昌龄录16首;杜甫却未收录。《国秀集》选录40人。李白、杜甫均未收录。类似情况因由颇多:一、历史需要沉淀,短短的时间,很难一锤定音;选家自有选家的目光,对于作品的品味与赏鉴,各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据别林斯基的见解,历史上一个新作家的出现,特别是他尚未站稳脚跟的时候,尊崇与诋毁,是与非的对立,是常相混杂的。普希金的出世如此,鲁迅作品的面世亦复如此。莎士比亚这位伟大的作家,曾被马克思誉为世界艺术顶峰之一,但是却被艺术大师的托尔斯泰认为:他的作品是“很糟的粗制滥造之作”。就此审视茅盾研究的历史或解读史,它的价值的浮沉,他的位置被不断地排定,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文学作品是解读史,就是不断地误读与正解,错位与匡正的历史。
就一定意义说,误读或者就是正解的前导。匡正许多误读现象,需要公允的态度,辨识的目光和更为重要的价值品评的尺度。我认为这个尺度就是历史的审美的准则。因为离开了作家与作品产生的时代和文化语境,便难以把握、领悟它的丰富内蕴和价值取向。例如说,茅盾的创作,大都产生于国难深重的年代,在这种情势下,作家的忧患、社会责任感,他作品中的公民视点和对民族命运的关住,无疑地是一种颇值得推崇的美德。这是因为作家不仅是人,而且是“祖国的公民,他的时代的儿子。民族和时代的精神对他的影响,不会比对别人更少,”。这对于置身于为难中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现实的事,无可回避的社会职责。因此,许多作家并非是“奴仆于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发自内心的启蒙与救亡的坦诚良知。
自然,这种忧患意识,是渗透在生活的体验和艺术建构的全部过程中的。对此,茅盾在《中国苏维埃与普罗文学之建设》和《<地泉>读后感》中曾反复的阐释着自己的论点。他认为在1928年到1930年间所出现的早期的革命浪漫蒂克文学的缺欠,就在于它们的“脸谱主义、”和“方程式”化。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一)缺乏社会现象全面的非片面的认识,(二)缺乏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他自己的艺术创造,从短篇《春蚕》到长篇《子夜》,无不精心地在历史与人的深度模式中,建构自己的艺术天地的。作为艺术风格的话语体式,是冷静而客观,富于理性特征的。寓情感于形象的体现之中的内蕴,是明晰可见的,所以无论是老通宝或者是吴荪甫形象塑造,都具有活脱而复杂的性格,从人物创造到社会的画面,形成历史与诗学的统一。就历史来说,他以一系列互补的长篇小说,在全景式的社会描绘中显示出现代中国动态的形象史的品格;而“诗学”的才情,则使他在创作上具有着驾驭宏大题材并深刻地洞察生活的力度。如果可以把文学创作,析离成社会、历史、心理和哲理的不同层面,那么以《子夜》为例,虽然不如《阿Q正转》所达到的哲理高度,但在社会、历史和心理的层面上,却是宏阔而深邃的。而其就商人和资产者的形象塑造来说,和阿Q、闰土等人物一起,活在现代文学的画廊中的。可以说,他继鲁迅之后,和同时代的小说巨匠,把中国现代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峰峦。
正是从这种历史的审美的氛围中,引发出许多有识之士,艺术品平的肯定的结论。捷克的朴实可认为,茅盾的创作,把中国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子夜》是那一时期创作的高峰。”俄罗斯语文学博士索罗金说“中国作家中大概,没有人描绘出中国历史上这大变动的几十年国家生活的如此辽阔多彩的画面,没有人描绘出几乎代表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如此五光十色的人物画廊。这一点特别适合90年代初期茅盾才华横溢的时代的作品”。日本的筱田一仕则认为,就总括作品的既坚牢又自由变幻的空间状况形成来说,茅盾在这个同一时代的中国作家中可谓最杰出的存在。筱田认为《子夜》是20世纪世界文学的十大巨著之一。
如果离开了时代和历史的文化语境,正形同于离开了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氛围来理解哥特式的建筑;或者离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历史,来观赏布鲁涅列斯奇所设计的巴契礼拜堂,都会造成文化时差和审美上的隔膜,其结果不免形成“误读现象”。
自然,这种“误读”现象,可以是无意识的,也可以是有意识的,就无意识误读说,解质(接受)主体,可能失之幼稚,或对文本的历史氛围缺乏慎深的理解,或习惯性的淡化历史的因素,从而造成作家或作品品评的价值偏离和失误。在批评中,很难都是四平八稳式的。还有一种是有意识的误读,这又可分为正价值取向与负价值取向二途。前者,可以以马克思在1861年致培·拉萨尔的信中所谈到的“曲解”一事为例。马克思认为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三一律,就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的意识的曲解之上的。“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期的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显然,法国理论家所构想的三一律,是有所选择的,是按照他们自己对艺术的需要来理解的。用布鲁姆的话说,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正是如此,他们要执意坚持这种主张。在我国“五·四”时期,鲁迅与茅盾等人对于尼采学说的解读与传播,具有同样这样的性质。他们对尼采的学说,有所阐发、有所接受,也有所扬弃,有所不讲。就尼采本文的整体意义来说,自然可视为一种有意识的误读,但是这种阐释与借鉴是本土化的,它具有着时代、社会的基因,因而会取得群众的认同。
但是,也有另一种解读倾向,值得重视:他们孤立地强化自我的感觉,甚至如有人宣称:我所批评的就是我自己。其结果,那立论可能是“新奇”的,造成所谓的“轰动效应”,但主体的过分膨胀的结果,必然导致文本(作品)——作家——历史(时代)与解读之间的偏离或错位,从而时期了科学价值的可信性。近年来,关于茅盾及其作品的不同解释,乃至位置的排定,即包孕这上述的因素。鲁迅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忌全篇,并且顾忌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成梦的”。这见解,至今仍是防止片面和误读的好办法。
二
诚然,文学的历史,总是过去发生的事,就此说来,历史与历史的解读也许永不相当。所以,克罗齐有所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对此,伽达默尔似乎更为悲观一些。他认为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法师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人,还是理解的对象——本文,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也就是说都是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中的。他甚至认为本文作者的原意是不存在的理解根本无法去复制本文作者的原意。对此,我以为赫施在《解释的有效性》中对本文的解释还是有道理的。他把本文分为含义和意义两个部分。其中含义具有确定性,凝结于本文之中,而本文的意义部分,却因时代的流变,接受者的取向不同,而处于变动不居的历史演化之中。
对于茅盾的研究也是如此。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风习的转化,对于茅盾及其作品的解读自然会不断演化,日月长新。甚至会出现向韦勒克所讲述的情况:“倘若今天我们可以会见莎士比亚,他谈创作《哈姆雷特》的意图可能使我们大失所望。我们任然有理由坚持在《哈姆雷特》中不断发现新意(而不仅是创造新意),这些新意很可能大大超过莎士比亚原先的创作意图”。这“发现”的“新意”,实际具有双重意旨:一是含义,它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可能是潜在的,或者是一种无意识状态,但无疑是确定性的存在。它以不同的方式隐匿着,自然会以不同的方式被揭示出来。同时,这本文的孕育与创造,又受制于他所诞生的文化关联域。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近乎这个道理。我们从作家的本文中,总是可以感觉到创作时的话语空间、生活理想以及人与世界的交互关联。茅盾的《蚀》三部曲是在革命文学勃兴时出现的;而《子夜》生成构建的文化氛围,则流布在新写实主义为文化正格或主潮的话语空间。《霜叶红于二月花》与萧红的《呼兰河传》等,都是与民族文化的剖解密切关联着的。由此可以说,现实解说中的意义,总是与本文的含义处于双重话语之中的。
是的,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现实在革命开放的形式下,人们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观察,已经把民族忧患的岁月推向过去了。同时对于“左”的思潮的反思也有意回归到文学本体、艺术审美情趣的轨道上来,因此对艺术的侧重与关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种纯而又纯的审美境域,究竟是难于存在的。试想,在文学的审美域中,如果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都析离出去,那文学中还存活着一些什么因素呢?与茅盾同时代的作家中沈从文是颇重视艺术的,他自己说:只想选山地坚硬的石头,建筑精致、结实、纯正的艺术殿堂,但是打开他营造的七彩楼台,依然不失人性、民情、静态的乡土风韵。只是在茅盾与沈从文之间,一方重于社会责任感,一方重于艺术风情而已。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都以互补的势头,存在于3年代小说世界中,如果我们无视这种实际,企图另行勾沉,那将失去本真的“文化语境”,也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所以,我认为历史的审美的准则,对茅盾以及不断解读的中国现代文学来说,都是必须的,切乎实际的。
仅就艺术风格审视,老舍的智慧的民俗的目光,巴金的激情的而又伦理的态度,沈从文的诗意与静态的乡土结构和茅盾的宏阔的史诗般风范,又恰成竞相发展之势。有人说,文学大厦的规模和高矮,是以一批巨人做它的柱子的。30年代的小说,如果“没有茅盾、巴金、老舍这些巨人,中国现代小说的大厦就要矮半截”。这语言也许并非科学的标书,但却满蕴着至理。
研究者认为,史家需要博识与通览,这博识要有共时的才情,而通览则需要历时的目光,还有一点就是宽容、公允的态度,这也许都是防止偏执、错位的误读的要素。对于茅盾的解读,自然也需要在历史纵横的焦点上加以剖解。我们没有必要为古人粉饰,却也不应失却历史的公正态度。人们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不难发现其中镶嵌的历史风云结构;同样的也含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看到他对金融和债券市场现金交易露骨的描写,其中自然有生活的本真向艺术的美与丑转化的成败得失问题,但在总体上这两位艺术大师的艺术价值与风范,在历史的天平上,已经得到认同。茅盾的创作,自然不能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比附,但在某些侧面上却也不无相似之处。茅盾小说对于历史对人的制约以及现今世界的把握,无疑是十分重视的,无论在艺术结构的组合中是否成功,都将构成这个作家的特点。我甚至想,如果失去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快节奏的观照,金钱趋动下社会张力的描写,历史风云的烘托,心里写实的刻画,那将不再是茅盾的创作。《腐蚀》是政治小说,也是心理写实小说,是两者的“复调”。对于性文化“情节”,在茅盾的小说中,也并不回避,因为多方的点染,对于资金制约下的社会的浓疮,自然没有老舍那般严肃,品位却并不低下。这一切都是个人化的、历史的。
历史在不断地进步,但历史的文化现象不应湮没。在历史、审美的解读中,茅盾及其作品的价值即便会有浮沉,但是他的客观价值也必将取得历史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