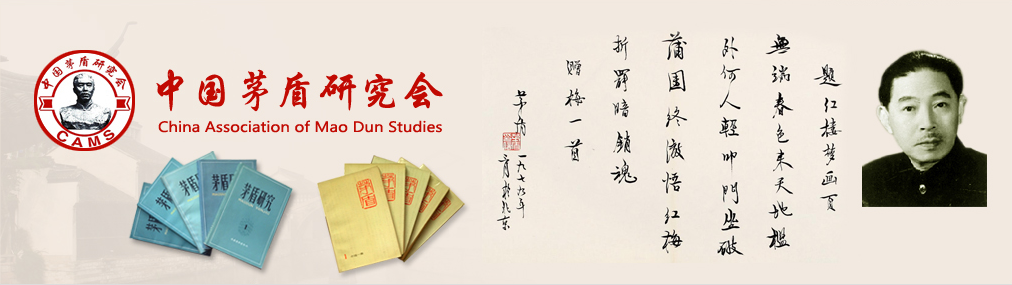对茅盾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钱诚一
屈指算来,在茅盾研究这块园地里已断断续续经营10多年了。我所思考的问题有三:
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
无论怎么说,茅盾都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作家,即以他从1921年算起的党龄和在“五·四”新文学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我们因而将他和鲁迅、郭沫若并称,公认他是新文学的又一面光辉旗帜,并对他由衷的仰慕和崇敬。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茅盾研究者说来,对茅公的这份感情,不仅是我们开始茅盾研究的原动力,更是我们甘于寂寞、至今守望着这方园地的精神支柱。其积极意义十分明显,更不可低估。但另一方面,对此我又时有这样的疑虑:它是否可能成为我们自设的精神障碍并影响研究的全面与深入?
这疑虑源于我对自己研究套路和学术心态的反思。我发现自己虽然明白评论作家须顾忌全人,既谈优长,也说缺欠,并深知后者同样是显示研究神广度的重要方面,但实际上却总是习惯于不断掘发和张扬茅盾的强点与成就而极少考虑深入揭示和评说他的弱点与不足;尽管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大师巨匠也有局限的事实,也明知可以对他们品头论足批判评说,可是一旦涉及茅盾的局限,就心情沉重,难以下笔,远不如张扬他的优长或评说其他作家的局限那么自信和轻松。论点固然再三掂量,特别慎重;措辞也是反复推敲,格外经心。而且即便如此,每每仍忐忑不安,仍怕亵渎茅公或有损他的英明。如果这种套路和心态唯我独有,当人无关大局,不足为虑。但遗憾的是,与我类同者似乎不在少数。这可以从许多茅盾研究论文中得到印证。究其缘由,也许并不简单。即从研究者自身考虑,亦未可一概而论。但以我之见,恐怕多半为情所累。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茅公的这份崇敬之情,既激起我们研究茅盾的强烈意愿并支撑我们坚持至今,但也成为我们拘囿自己的精神障碍并使我们开首就丧失了一种敢于揭“短”挑“刺”、批评大师的胆量和气度。
虽然我至今怀疑是否真有不带任何情感倾向的所谓“零度感情”的作家评论,但我认为研究者过多的情感投入,确实会影响评价的客观、全面和公正。当我们满怀崇拜敬仰之情投身茅盾研究时,必然虔诚地仰视对象而舍弃其它视角,但仅此一种观照角度,非独限制视野而且难以与对象建构作家评论必须的平等对话关系;与此相应,也必然以张扬对象为己任,而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责任心,以及单一的仰视角度,势必酿成我们研究路径的偏至并在无形中能化学术研究应有的批判锋芒(就“批判”这个词语本身的意义而言)。那么,我们如何让还能大胆地逼视和叩问对象而毫无亵渎大师冒犯尊长的不安?除了热情张扬对象的强点和成就,我们如何还能深入评析他的弱点和局限,或者心平气和地认真倾听那些与我们不尽相同的批判?除了继续重复已有的成说和定论,我们还能有所发现并把茅盾研究不断向深广两个方面推进?
我决不是轻薄和非难崇敬茅公的纯真感情,更不是诱导或煽动贬损茅公的轻狂行径。因为我确信,茅公是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爱戴的大师,我们不该因为苍鹰有时飞得比山鸡还低,就说苍鹰不如山鸡能飞。
茅公无疑是一株参天的大树,而我们只是一片低矮的丛林或贴地的小草。但我们无须因此自惭形秽,除了敬仰爱戴,别无作为。沈尹默《月夜》中的两句诗说得好:“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面对大师巨擘,我们应该发扬这种独立不倚的自主精神,敢于平等对话,如实批评。敬仰,但并不顶礼膜拜;爱戴,而并不曲意回护。俗话说,智者千虑难免一失,愚人百思或有一得。更何况,与茅公所处的那些岁月相比,今天我们确实站在高处。时代已经为茅盾研究的创新开辟了多种路径和广阔前景,能否有新的创获,关键首先在我们自己。
二、当代性与历史主义意识的关系
如今,茅盾研究已日益呈现出“史”的研究的特点。虽然作为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专题,它有不同于一般历史研究的特殊性,具有更多的主观性和个人色彩。但既属历史研究范畴,应当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这中间有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当代性与历史主义意识的关系就颇费思量。
历史是业已终了的过程,是既往和过去,要将他照样复原和再现,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段历史,其实都不过是前人或我们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一种描述与评析。这种描述和评析,除了依据确凿可靠的历史事实和文化传统所提供的那一套约定俗成的评判标准,主要是受制于前人或自己当时所具有的价值观、历史观以及对具体史实的识见。而且,任何对历史的描述与评析,又总是从彼时彼地或此时此地的现实需要出发的。因此,他们不仅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更呈现出鲜明的当代性。这在对历史的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中尤为突出。正是基于此,我认为克罗齐所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和“当代史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的说法,确实不无道理。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历史(包括文学史)也不是认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不仅业已确定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而且历史演进的法则和规律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可以凭借当代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水平,重新审视个评价历史事实,重新研究和把握历史规律,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和有所变化。但无论怎样深入和变化,确定的史实不能重新改写,客观的规律不能主观外加。承认历史研究的主观性,决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信口开河,而是为了开拓不断逼近历史真实的多种途径;强调历史研究的当代性,也绝不意味着可以割断当代与历史的内在联系而是为了从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中揭示更多的历史真谛。
基于对历史和历史研究的这种认识,我认为,在茅盾研究中,既要强调当代性,但同时也要增强历史主义意识,并要力求使两者在追求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的基点上统一起来。
要使茅盾研究更具当代性,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和宽阔的胸襟,大胆吸纳当代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规范,已更新、丰富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和评估体系。但这并非唯新是骜不加选择地让各色新潮理论乃至种种玄谈妄说都到这块园地里来信马由缰地任意驰骋,而要从茅盾研究的实际出发,对它们详审细察吐纳扬气(这一点后面还要具体说);这也并非舍本逐末虚张声势,只是挦扯几个新名词洋概念来装幌子装点门面,而是从批评操作手段到文学思想、哲学观念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深刻变易。否则,包装虽新,但货色依旧,还是不中用的。
不清楚地基上的断墙残垣陈年垃圾,新建筑就没有安身之地;不打破思想上的条条框框陈规旧习,接纳新潮也将是空话一句。因此,必须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继续清除庸俗社会学、机械唯物论一类陈规旧说的恶劣影响,特别是彻底改变我们长期以来在接受那些荒唐说教中形成的封闭僵化、充满惰性的研究思路。各种陈谷旧说非但历史悠久,而且影响巨深,要彻底肃清它们的影响,很不容易;而要真正超越自己,彻底改变我们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套路,更加不易。回顾我自己,就每每是立志要走新路,但迈的却是旧步,走的仍是老路;有事甚至眼看跨上了新路,可一不小心又折回了故道。我们在旧格局中毕竟盘桓已久,老套子已经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旧思路早已驾轻就熟融会贯通;而新观念新规范新方法我们才刚刚“拿来”尚不熟悉,更何况时而还有他们来路不正的传言,弄得我们满腹狐疑,三心二意。就茅盾研究的现状来说,改变旧思路也许比引进新观念更加迫切。因为倘不彻底改变这种蔽塞心智、窒息个性、钝化学术敏感的旧思路,那么,无论多么富有当代性的神思妙想、良规新说,都可能因为我们的冥顽不灵而无缘相识,即使当面相遇却仍错身而过,失之交臂。
这里还须将各种挣脱旧套另辟蹊径的严肃尝试,同那些蔑视真理、糟蹋前人、一味鹜新趋时的轻狂浮浪之举细加区别。对于前者,我们应以更多的宽容和谦虚,与他们切磋商讨择优采取;而不要守旧排异自设藩篱,将他们拒之门外干脆不理;或以“不全宁无”的偏执态度,对他们百般挑剔一概摒弃;更不要把它们学术上的问题硬扯到政治上去乱批。因为这些态度和做派都与当代意识格格不入,而是地地道道的传统积习。
增强历史主义意识,并不是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一类说辞宽谅历史,而是要自觉地意识到“当代”是“历史”的逻辑发展,两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无论用多么富有当代性的意识描述评析对象,都不能离开历史实际。具体到茅盾研究即要求研究者在以各种当代思想观念描述评析茅盾及其创作时,不仅顾忌作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作品反映的生活实际,并且坚持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审度和衡定他的长短得失以及地位价值。这需要研究者 立足于对整部文学史(特别是现代文学史)的理解和感悟,具有一种能同时感知远古与现在的纵深的历史感。任何一个国家,一部作品都不可能四顾茫茫地独自存在,也不可能单独有他(它)自己的完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既存在于他作品的文本以及读者对他的解读中,更存在于他(它)同已往与后来一系列作家作品的关系中,并通过对这些关系的评价充分显示出来。文学史上一系列漫长连锁的作家作品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参照系,具有历史主义意识的研究者把对象置于其间并从纵横两个向度上进行对照比较。这种比较,既不是纵向的以古例今或以今绳古,也不是横向的纯粹审美特征方面的品题评量,而是对不同作家审美的把握和表现现实的深度、广度、迅速程度以及独创性程度的相互计较。只有从这种历史性的衡量中,研究者才能对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意义或价值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倘若离开了这一参照,就难以测定他(它)在文学史这个系统中的准确位置,也势必影响到评价的准确可靠。不仅如此,这个参照系所具有的巨大历史性力量,又在无形中制约着研究者描述的措辞和评价的分寸。一旦失去这种制约,研究者就很容易轻率地给对象种种以不切实际的褒贬抑扬。前些年“重评《子夜》”中的有些偏颇,我认为这是缺乏历史主义意识所造成的。譬如有位论者以“情节斗争化”为病而否定《子夜》,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论者无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实际——30年代初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斗争错综交织的历史事实,却指责作家“在政治观念的指引下”,“戴上‘阶级’的滤色镜与‘斗争’的变色镜,在作品中伪造生活”;也无视古今中外几乎没有哪一部长篇小说(包括为论者所推崇并时常称引的卡夫卡的作品)是不写斗争(包括阶级斗争)的文学史的事实,而把一部在广阔的背景下,艺术的表现半封建半殖民地大都会上海及江浙农村现实矛盾斗争的成功的现实主义小说,斥之为“非艺术的‘伪长篇’”。这种置确凿的历史事实于不顾,一味强调所谓“当代性”而缺乏最起码的历史主义意识的批评,其偏颇是十分明显的,当时也是使人不能苟同的。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关系
现在回顾85年前后兴起的文学研究新方法热,其稚拙肤浅的一面确乎相当显眼。但平心而论,它在引进域外文学研究的良规新说和移植其它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以打破传统社会学批评范式的一统天下,形成文学研究方法多元并存的格局方面,却功不可没。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不少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更新一集由此引起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审美视野的拓展。但与当时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生气勃勃的热闹景象相比,茅盾研究这块园地里却多少显得有些沉寂。是茅盾研究界思想僵化、冥顽不灵?还是谨慎有余、过分矜持?抑或是此外别有原因?可是,当时焦虑不安的情绪却是我无法定下心来对此细加思量,只顾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直到不仅经历了自己、而且见过了别人若干不成功的探索尝试后,我才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其中的缘由并对当时的“沉寂”也多少有了一些新的理解。譬如说,因为还得考虑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是否互相契合的问题。
黑格尔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管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而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众多方法中,除了作家生平和作品版本的考订这类方法外,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指示相应的美学范畴,具有一套特定的审美标准和概念结构,并与研究对象构成一种对应关系。因此,研究者在运用某种方法于对象时必须考虑方法与对象间的同一性问题,既考虑方法之于对象适用性和可行性。譬如,对于茅盾小说就很难诉诸“神话原型”的研究方法,而用社会评价的方法也难以窥测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天地。
如果说,对总体而言茅盾地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这一点没有异议,那么,社会评价在茅盾研究中就大有用武之地而不该全然丢弃。这很可能有思想僵化、保守传统之讥。因为社会批评一度确乎成了传统批评的化身,而在一些新潮批评家们看来它是早该“派斯”的成年垃圾。但我认为,社会批评至今不失为一种有深度并仍富活力的批评方法。批评史的事实证明,,尽管新的批评方法旗幡林立层出不穷,但社会批评却并未因此悄然引退。这恐怕未必全在政治权威的力量,更重要的,还在它自身研究途径与程序的科学性,以及文学与社会那种内在的关联性——两者永远割不断的联系。连对社会批评颇具訾议的美国文论家魏伯·司各特也承认:“只要文学保持着与社会的联系——永远会如此——社会批评无论具有特定的理论与否,都将是文艺批评中的一支活跃力量”。但是,社会批评所擅长的社会历史分析和现实政治(有时还兼道德)评判,并没有穷尽文学的全部奥秘。譬如,深入了揭橥了《多角关系》中人物间的矛盾纠葛与当时社会现实经济关系的同构性和对应程度,或精辟评析了吴荪甫败北和林老板破产的时代历史动因以及蕴含其中的深刻思想主题,并不意味着已经完整地解释了这些作品。因为即便成功地揭示了一部小说政治层面的全部意蕴,也未必就已经完全领会了它的美学意义。而从审美的角度对作家作品进行描述与评析,正是社会批评的短处和缺欠所在。因此,对于茅盾研究来说,选择与社会批评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美学——历史”批评十分注意研究作家、作品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总是把作家作品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进行考察,既作周密详尽的历史观照和社会批评,又作深入细致的艺术分析和审美评价,并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互相联系,紧密结合,把两种价值判断具体地体现在同一批评对象身上,在两种的统一中实现对艺术的整体把握,进而估定对象的全部意义和价值甚至提出一些具有根本性的或普遍意义的问题。这种研究方法为充分揭示茅盾创作与社会、与时代历史的广泛联系和作品自身蕴含的富有创造性的美学价值开辟了切实的途径。“美学——历史”批评并不是新方法,但茅盾研究的实践证明,这种方法非但没有过时或失效,而且随着研究者熟练程度和操作水平的提高,日益显示出高度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这也表明,研究方法虽有形成或流行时序上的先后之分,但并非一定具有相应的价值上的高低之别。老方法未必就一定比新方法逊色,新方法也不见得注定比老方法高明。一些运用新方法论析鲁迅现实主义的文章,我看在深刻性上就并没有超过陈涌那篇用老方法写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这使我后来对茅盾研究园地的“沉寂”在焦虑之于又多少有些暗自欣喜。庆幸我们没有生吞活剥信息论的“反馈”说,使茅盾在我们笔下沦为一个探头探脑专门打听文坛行情的投机小贩,也没有异想天开地用一个莫名其妙的公式外加一番眼花缭乱的运算去厘定“时代女性”的审美价值,或别出心裁地以“圆心结构”、“链型结构”之类的几何图形来归结茅盾的小说结构的美学意义……。
当然,说社会批评在茅盾研究中仍然大有用武之地,“美学——历史”批评比其他方法具有更多的优越性,说新方法未必一定比老方法高明,甚至弄得不好还会出洋相闹笑话,但这决不是说我们的研究方法业已尽善尽美并足够有余,引进新方法非但多此一举而且纯属奢侈。绝非如此。因为无论多么精妙完美的研究方法,都不可能单枪匹马精确无误地遍丈艺术的广袤领地,独自穷尽缪斯的全部奥秘。任何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方法,都既有独擅胜场的拿手之处,也有难以顾及的理论盲区。面对茅盾这样一个一个奇奥博大的艺术存在,单单采用一种研究方法势必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明智的做法是博采众长,充分发挥各种研究方法的特长和优势,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展开研究,并在通力合作互相协同中实现全面的综合。即便是一些局限明显相当片面的研究方法,只要确有独到之处,并对某个具体环节的研究有所推进,就不该弃之不顾而应当积极择取。譬如,形式主义批评对作品语言及自身美学结构的细致研究,心里批评对作家内心隐秘和读者审美心理的深入发掘,结构主义批评的有机整体观和对作品形式规律的执著探寻,难道不能弥补社会或“美学——历史”批评的若干缺欠,并进一步开示茅盾研究中这些原先较少涉及的话题,甚至孕育突破旧局的某些新机?曾有人循着作品(叙事结构)——作家(心里状态)——历史(文化)的线索,尝试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茅盾,也许我们未必赞同作者的全部观点,但这种尝试本身,却不失为一条窥探和把握茅盾创作心理的切实途径;也曾有人用结构主义方法重评《子夜》,尽管我们对作者的结论不敢苟同,但应该承认,这种方法对于纠正作品研究中割裂内容与形式的偏颇,却不无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