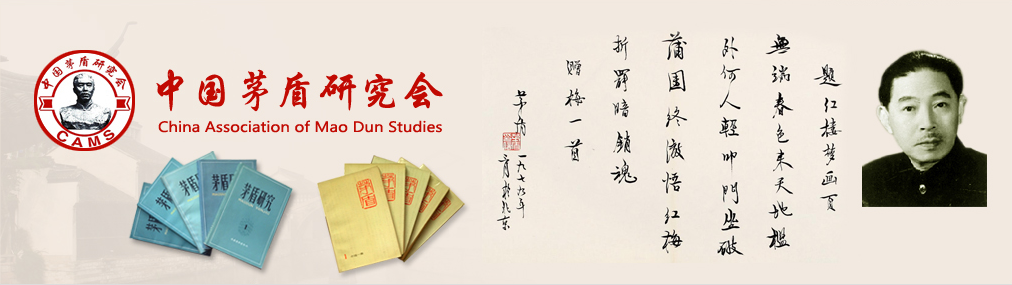人生体验促进研究升华——茅盾研究和我(节录)
丁尔纲
四
50年代后半,国际上掀起反共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有些共产党也开始和平演变。中国的对策是反修防修;其中也夹杂着极“左”思潮。“文革”则达到极致。这对茅盾,对我和我的茅盾研究,都是一次大冲击。在目睹亲历这段历史中,我形成了自觉的思潮意识。新时期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西方各种思潮一齐涌进。其中包括早就产生,滞后涌入中国的成分。如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冲击最大的是1961年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版,1979年香港友联出版社中文版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时此书在大陆流传,就引起了混乱。夏志清标榜“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评价作家作品,反对“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差”。但他又宣布:“我自己一向也是反共的”,我在书中“讨论有代表性的共产党作家、并对共产党在文艺界的巨大影响力作详细的交待,可是我的目标是反驳(而不是肯定)。”这也难怪。夏志清1951年曾受雇于美国政府以政府提供的经费编写《中国手册》,供美国政府向侵朝美国军官进行反共宣传用。他抱着反共与反驳共产党对中国文艺界的影响之目的治《中国现代小说史》,其反共倾向就使他偏离了他标榜的“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的标准。全书的“反共宣传”基调,使此书成为五六十年代国际反共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本书在中国的滞后流传,冲击了新时期的中国文坛。
由于我是这两段思潮史的目睹亲历者。敏锐的思潮意识使我及时发现:此书在大陆传播过程中,与当时针对极“左”思潮及其危害的“逆反心理”发生了共鸣。特别是使某些没有思潮经验的文学青年发生了思想混乱,右向逆转到另一极端,出于责任感与参与意识,我立即把刚恢复的茅盾研究与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结合起来。先以茅盾研究与评价夏著为切入点参予论争;想借此力避文坛逆转的不良取向。
我先写了《艺术探索与政治偏见之间的徘徊倾斜——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茅盾专章》。接着写了两篇评夏著全书的文章,与两篇针对夏著及当时国内外否定鲁迅的社会思潮的文章。后来结集为《新时期文学思潮论》,这组文章编为上编。中编与下编则是由此延伸,总结现代文学思潮史经验,针对当前文坛走向的文章,思潮意识与“史识”使我抓住了夏著的要害。我在文革中承认,当时在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史的史著与教学中,确实存在论述民主主义作家与敌对营垒作家覆盖面不广的“左”的偏向。但夏志清站在其自称的反共立场上反其道而行之的倾向,也是违背历史主义与科学态度的。我指出其主要表现是:一,对“五·四”新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的解放区文学,除具反封建倾向者外,大都以“这是宣传”为籍口持否定、基本否定或贬低态度。二,贬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为地抬高或拔高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师陀等。不仅把两类作家相提并论,甚至把后者置于前者之上。特别是拔高张爱玲,不仅冠以“最伟大的”、“最杰出的”、“最好的”等等最高级形容词,把她置诸世界文学大师行列,而且在承认《秧歌》、《赤地之恋》两部长篇是“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的概念化小说”的前提下,仍对其歪曲新中国的真实面貌把它写成“共党统治下”“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残的记录”的这两部长篇的反共倾向倍加称赞。三,在论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时,对其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的创作还予肯定,对其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的创作则几乎全盘否定。对其后期的思想取向大都贬为“共党宣传”。四,对茅盾前期著作加以曲解,如其《动摇》中人物方罗兰有段攻击工农运动的话。茅盾的批判描写,竟被夏志清曲解为茅盾假借方罗兰之口,揭露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是“暴政可恶”!五,对茅盾的政治与艺术态度也加以歪曲。一方面把其无产阶级倾向说成是“共党宣传”,一方面又说茅盾为保持“中共作家中首席地位”而“言不由衷”;实际上存在游离以至反对共产党的倾向。这是后来有些人所说的“茅盾双重人格论”之本源所在。
我在文章中坦率指出:夏志清这些歪曲文学史真实、任意抬高或贬低许多作家作品的文学价值、文学史地位的做法,表面看他是违背了他“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的自我标榜;实质上都是“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故意为之导致的“偏差”。我还指出:夏志清此书的反共倾向使他离开了学术研究,是他自觉配合国际上掀起的那股反共思潮的具明显政治功利目的之作。因而有必要把他这部书和此书产生的客观影响与共鸣区别开来;和与之产生“共鸣”的国内反对“文革”前即有的文坛的极“左”思潮的那种“逆反心理”,严格区别开来。
这样,这些文章在当时澄清文坛上与社会上各种思潮大碰撞导致的许多混乱现象与糊涂认识方面,在澄清现代文学史、特别是茅盾研究领域与此有关的分歧意见方面,多少起到一些作用。
五
进入新时期后,茅盾的历史地位与茅盾研究中的公认的评价,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其最大者是两次。一次是从提出“重写文学史”到最近作为其余波推出的重新“排座次”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先是从各方面贬低和非难茅盾及其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后来则干脆把他从文学大师队伍中“除名”。为意识到这是新时期文艺思潮中比较重大的现象,先后发表了《拨开云遮雾罩,恢复庐山真貌——评近些年茅盾研究中的某些观点》和《闻茅盾被〈大师文库〉除名有感》两篇长文。对贬低与曲解茅盾及其作品的某些观点予以辨析。鉴于持这些观点,采取这些做法的,大都是没有文学思潮跟踪研究经历与体验的年青学者,因此我采取平等商榷的学术探讨态度,文章也以正面立论为主,兼及错误观点与曲解茅盾及其作品的说法的批评与讨论。我固然重视对这些误认与曲解的拨乱反正,但更重视这种文学思潮取向的成因的考察。在我看来,贬低或不承认茅盾及其作品的思想艺术贡献与历史地位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四点:一,与茅盾及其作品的思想政治倾向持对立观点,或淡化思想内容的非政治倾向。在为“重写文学史”作准备的一批论文中,从反对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开始,发展到否定文学史上具鲜明无产阶级倾向的作家如丁玲、周立波、赵树理以至郭沫若、茅盾的态势,一时之间形成文坛一个不大不小的气候。这些文章往往从今天的强调艺术、忽视政治的欣赏口味出发,来要求与衡量前人。二,对历史上应中国革命需要,在打击敌人、支持人民革命过程中,产生过重大战斗作用的作家作品的历史作用,采取不承认态度。甚至脱离作家作品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把它纳入今天自己的欣赏标准与口味中,合则褒,不合则贬。这种随意性颇大的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评判态度与标准,使其失却了客观的科学尺度。三,对待复杂多元的文学思潮现象,持合我者褒,不合我者贬的狭隘的艺术功利眼光与态度。往往从特定思潮与流派的主体倾向于需要出发。对非本流派的文艺持排斥态度,其批评多是“以尺论斤”的“异元批评”与“夸元批评”。四,趋时媚俗赶浪头的态度与无原则、随风倒的哗众取宠态度。凡此种种,或是政治取向不健康,或是艺术态度不严肃。其综合性后果,就是作历史评价时的随意性与主观片面性。不从这些病根作治本之医疗,文学思潮中随意评价历史、随意褒贬前人之弊难以根治。
另一次则是写文坛回忆录与为作家立传中对茅盾的歪曲。此事始自“文革”中批评茅盾时,秦德君提供歪曲茅盾政治历史真貌的材料。茅盾逝世后她又在国内外发表回忆录谈话录,沈卫威根据秦德君提供的片面的失真的材料所写由台湾出版的《艰辛的人生——茅盾传》,又总其大成。这些文章或从政治上给茅盾扣了“叛党”、“携南昌起义公款潜逃”、“把当蒋介石秘书当作人生最大追求”等帽子;或从人格与私生活给茅盾身上泼了不少污水。究其原因,在秦德君,主要是因过去的恩恩怨怨,心理不平衡,而挟嫌报复,在其他论者,则除了治学态度不严肃外,与标新立异、借披露隐私以哗众取宠的卑微功利目的不无关系。
由于事关中国革命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真实面貌与茅盾研究求真求实的严肃性与历史评价的公正性等大问题,我冒着卷进文坛纠葛的危险性,先写了一篇考证性论文发表在刚出版的《茅盾研究》第6期,又在今年出版的《茅盾——孔德沚》一书中,以正面阐述与描写为主,兼及辩诬去伪,拨乱反正。力争据实恢复茅盾的真实面目,澄清被搅浑了的文坛之“水”。
如果说前一次冲击还不失文学探讨的严肃性;那么后一次冲击则与世风日下、道德水准下滑的总趋势不无关系。因此,不论哪一次,都有严肃对待之必要。无论对发展茅盾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事业说,都是时代与历史之所需。
六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起码在阶级意识尖锐对立的整个20世纪,难以摆脱其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属性。对文学的评价,也不存在统一的政治标准。因此作家作品及其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就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文学艺术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现象,其评价则不是没有基本统一的审美标准。而历史的最终评判,将能作出客观的科学的评价。
茅盾作为无法抹煞与否认的文学大师。他对中国人民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他的文学建树,他所营构的理论世界与艺术世界,是充满思想艺术魅力的客观存在。尽管他不是没有局部的败笔或失误,但总体说他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将永远屹立在世界文学之林。后人因各自的社会政治观念与审美取向的歧异,在仰视时所感到的,有的是巨大的精神鼓舞与审美享受;有的则是精神压抑与审美逆反心理。因此,对茅盾的评价,难免相左或针锋相对。
但茅盾还是茅盾,或誉或毁或褒或贬,那是读者与论者的主观选择与取向,都不影响茅盾的文学史地位与历史价值。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潮斗争中,茅盾的幸运与厄运,源于他的伟大贡献及其对不同人的不同影响;他的伟大贡献,过去、现在、将来,都已经或仍将给他带来幸运或厄运。
但无论是这幸运或厄运,都不是茅盾的不幸,而是他享有的历史性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