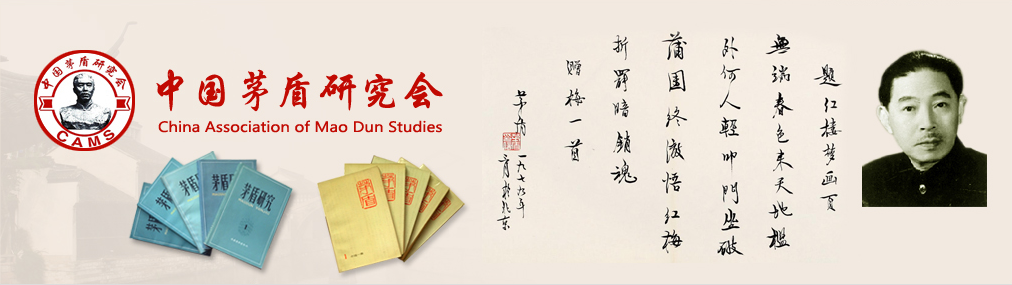漫谈我的茅盾研究心得——兼论茅盾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节录)
邵伯周
二、茅盾几部重要作品的评价问题
首先谈谈如何看待茅盾的有关自述问题。
作家的自述,包括创作经过、创作意图、创作经验以及为自己作品写的序、跋等等,和作品一样,是研究作家作品的第一手材料。
对茅盾作品的研究,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研究者们大都是这样看的。
在《从牯岭到东京》这篇长文里,茅盾除了申述自己对当时正在争论的“革命文学”问题的看法外,主要是申述《幻灭》等三部作品的创作经过、当时的思想情绪和创作意图。他说他的创作意图就是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阶段”即“幻灭”、“动摇”和“追求”。过去不少研究者在研究这三部作品时,大都是根据作家的自述来进行分析,谈到主题时总是回到作家自述的创作意图上面来。认为就是“幻灭”、“动摇”和“追求”。其实,如果仔细研究作品本身就会发现不是这样,《幻灭》、《动摇》、《追求》三部作品的主题实际上依次是“追求”、“动摇”和“幻灭”。笔者已撰文论述了这一看法,理由这里就从略了。《<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子夜·后记》等文章所说明的《子夜》的创作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并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对托派的回答作为主题。研究者们虽然对某些细节的看法还有一些分歧,但在总体上大家都承认作家的创作意图在艺术上是得到完满体现的,《子夜》是一部杰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1952年间,茅盾为他的一本选集写了篇《自序》。对自己过去的作品作了新的自我评价。关于《幻灭》等三部小说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说《幻灭》等三部小说是有生活经验作基础的。大革命时期他因工作关系一方面和当时革命的领导核心有较多的接触,另一方面又经常和基层组织和群众发生关系。因此,他有可能了解全面,有可能作比较深刻的分析的。二是说表现在《幻灭》和《动摇》里面的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有错误的,对于革命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表现在《追求》里面的大革命失败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也是既不全面而且又错误地过分强调了悲观、怀疑、颓废的倾向,且不给以有力的批判。三是说当时的生活中肯定是有下面人物的,但作品中却没有出现,原因是他当时的思想情绪是悲观失望的,这就必然要忽略他们的存在。个人认为对这三点应作具体分析。应该说第一点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第二点是既有正确的成分,又有错误的成分。应该说《幻灭》对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正确的,而《动摇》则不但正确,而且是深刻的——投机分子以极“左”的面目出殡,利用革命政策和革命者思想的动摇混入革命阵营,夺取权力,制造混乱,谋取私利的情况不仅在当时看到的人并不多,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反映这一历史现实的作品。《幻灭》对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反映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当时有坚定地继续革命的,也还有叛徒。我认为要求作全面反映是不合理的。至于说作品对悲观、怀疑、颓废的倾向批判不力的情况则是确实存在的。至于第三点可说是又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生活中确实有不少正面人物,但在作品中却没有出现(李克只出现一会儿,县不是主要人物),说不对,是因为一部作品不是非写正面人物不可,更不应以是否出现正面人物来评价作品。如果这样,又如何评价《阿Q正传》呢?
在这篇《自序》中,关于《子夜》的自我评价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说这部小说描写买办金融资本家和反动工业资本家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作群众的部分则差多了。因为后者仅凭第二手材料。二是说《子夜》最大的毛病还在于:一是虽然企图分析并批判那时的城市革命工作而结果分析批判都不深入;二是“未能表现出那时候的整个革命形势”,特别是因为在创作过程中改变了计划,写农村的部分没有展开,写农民暴动的第四章因已写好又舍不得割弃,因而在全书中成为游离部分,破坏了全书的有机结构。我认为第一点是实事求是,符合作品实际的,第二点则是不对的。众所周知,1930年时的城市革命工作是受极“左”路线指导的,茅盾写《子夜》时(1932年)党中央仍在极“左”路线统治了。党中央是在十多年后延安整风运动中才加以系统批判的。茅盾当年就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分析批判,尽管在描写上还存在一些缺陷,已经是极其难能可贵了,体现了一位革命作家的胆识与魄力。农村革命的全局被作为背景,而第四章则作为一个点来描写,这样点面结合,还是反映了当时的整个革命形势的,因而第四章也不能说是全书的游离部分。
在这篇《自序》中茅盾还总结了自己创作失败的教训,还说了一些自责的话,比如说:“年复一年,由于自己的决心与毅力两俱不足,始终因循拖延,没有把自己改造好”等等。如果从作家严于律已的态度来看,这种自责是无可厚非的。他所总结出的教训也是应该肯定的。但作家对自己某些作品如《蚀》、《子夜》等所作的自我评价,评论者是否可以据此评价有关作品呢?对一过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必须了解茅盾写作这篇《自序》的历史背景。1951年向全国文艺界展开了整风运动,1952年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在理论上说是要求知识分子与三大敌人划清界线,改造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改正工作。在这个运动中,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如不作自我批评、深刻检讨,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那是过不了“关”的。作家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自然就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当时许多著名老作家也都是这样做的。作为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能不自我批判、自我检讨吗?这篇《自序》,实质上就是茅盾在这一背景下的自我批判、自我检讨。我相信这在茅盾自己,是真诚的,并不是为了过“关”。但在研究茅盾的作品时,可以不作分析就把这类自我批判作为评价有关作品的根据吗?遗憾的是过去有不少评论者(包括我本人)正是这样做的。我现在认为对此必须考虑到历史背景,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而又有所取舍。
总之,作家的自述材料以及自我批评之类,虽然是研究作品的第一手材料,但只能作为参考,分析作品还应该从作品本身出发,当然还应该做到如鲁迅所说的“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
其次是谈谈如何看待某些评论文章所提出的独特见解。
80年代末在茅盾研究领域出现了几篇评论文章,对《子夜》、《春蚕》等茅盾的代表作提出了新的评价。见解独特,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曾有一位评论家对某几篇的论点提出商榷。5年多来,对那些独特见解,似乎反响并不大,是不是已被默认了呢?也不见得。鲁迅曾经指出:批评家都有一定的“圈子”,“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个人感兴趣的并不在那几位评论家对作品的评价如何,而在于想探讨一下他们用的是什么“圈子”,这些“圈子”对不对。
这里说的80年代末出现的独特见解的几篇评论文章指的是:王晓明的《一个引人深思的矛盾——论茅盾的小说创作》、汪晖的《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徐循华的《诱惑与困境》和《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一个形式考察——关于<子夜>模式》、蓝棣之的《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下面把这五篇论文分为四组来加以考察。
“遭到艺术女神拒绝”论。
“王文”认为只有作家的“急不可耐地只想发泄的情感”得到“发泄”,“才真正称得上艺术创造,才可能产生出艺术精品”。而茅盾早年就是一个热心社会活动的人,他从事文学就是想以文学为工具来改造社会。他是抱着“狭隘的功利目的”和“非审美”观点从事创作的,因此很可能会“遭到艺术女神的拒绝”。他认为《幻灭》、《动摇》内部都存在“许多不协调地方。”从写得好的方面来看,那就是大革命失败后的失望、苦闷情绪和他以前对女性魅力的“情绪记忆”得到了“发泄”的结果。而《追求》则是他的“幻灭情绪逐渐深化”并达到“审美理解”的结果。那么,《幻灭》等三部小说到底应怎样评价呢?“王文”没有作出明确的判断。但是它认为从写作《幻灭》到《追求》的一年间,茅盾在内心完成了从政治活动家到小说家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就是“艺术创作的激情”(按:指悲观、幻灭等个人情绪、对女性肉体魅力的感受以及对弱者的同情等等)“压制住了政治热情”,也就是没有为艺术女神所拒绝,从而显示出他那“与众不同的艺术风姿”。
“王文”认为《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几乎每一个作品都具有相当明确的社会政治主题。因为这时候他已“舍弃自己擅长的情感体验,按照一个既定的主题来写小说”。也就是用“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来创作”了。那么小说是否成功呢?论文也没作出明确的评价,而是把评价寓于分析中。就《子夜》来说,论文认为有两个吴荪甫:在工商界活动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其他资本家一样都是概念化的。“在书房中独自一人”,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子”的吴荪甫,他暴躁、沮丧、虚弱,并且“兽性大发”,这个形象是“使人感到可信”的,因为体现了作家的“感情体验”,对一些女性形象如林佩瑶、四小姐的心理描写,也是成功的,因为这些再一次体现了作家“那种宣染女性肉体魅力”的能力。至于小说的基本情节,也不是“来自预先形成的抽象命题”,即不是表现主题的需要,而是为作家的“艺术个性和情绪记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表现“明确的社会政治主题”的部分都是概念化的,而按照个人“情感体验”写的部分(包括人物和情节)则是成功的。总的来说,茅盾写作《子夜》等作品,是“遭到艺术女神的拒绝”了。论文还按照这个原则论述了茅盾40年代写的《腐蚀》等作品。
“王文”没有引经据典,它的理论基础和批评标准就只能推测了。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的意识有三个层次,即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意识是人的自觉活动,受社会舆论和伦理道德的影响;潜意识即性爱,包括人的原始的盲目的冲动、其他各种本能以及被压抑的欲望;前意识则介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起调节的作用。费洛依德把潜意识看得非常重要,是他的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内容。他据此认为文艺创作活动就是要使受压抑的精神得以松弛,被箝制的本能如性欲等得到渲泄,从而使作者和读者得到一种“补偿”,达到变相的满足。所以他认为“一篇作品就和一场白日梦一样”。上述“王文”的许多论点是他的独创还是源自费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不敢妄断,但说和精神分析学说有十分相似之处,则是毫无疑问的。
“背离‘五·四’文学传统”论。
“汪文”认为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构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茅盾传统’的东西”,从而“背离”、“歪曲”、“抛弃”了“五·四”文学传统。事实果真如此吗?
所谓“五·四”文学传统,从思想意义上的角度说,是反帝反封建,也就是宣传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从文学思潮的角度说,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主要是现实主义。这已是人们的共识,或者说已是常识,没有必要再加论证了。可是“王文”却有其独特看法。
“汪文”认为“五·四”文学传统,一是对待现实态度的“个人性”,即“作家对人生问题的思索源发于个体对生活和自我的直觉观察”和由此产生的理解,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却处于一种模糊、混沌的状态”。二是对待个人态度方面(其实是题材方面)是“写小人物”。它认为“‘五·四’文学以鲁迅为代表的小说,始终注目于小人物,不仅没有出现英雄,而且也没有表达对于英雄的期待”。郭沫若的诗歌也是“反英雄”的。三是“主观抒情性”。因为“‘五·四’小说在叙事过程中,特别强调了‘我’与现实的关系,‘我’对‘现实’的感觉、体验和观察”,“五·四”文学中大量第一人称的出现,“正是这称主观抒情性的必然表现”。说实在的,上述三种情况是存在的,但只是“五·四”文学中的部分现象,更不是内在的本质,有的甚至还可说是某种局限性。“汪文”把这些说成是“五·四”文学传统,是似是而非、以偏概全、以现象代本质的说法,才是歪曲了“五·四”文学传统。那么,“汪文”所说的“茅盾传统”(或说“《子夜》模式”)又是什么呢?用“汪文”的说法:一是“在明晰的、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用艺术的方式剖析这个社会及其各阶层的运动”,从而使小说“呈现出政治意识的明晰性、系统性”,“大大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论辩性”,因此使“个人性”失去了意义。真不懂这是什么逻辑。二是《子夜》写了许多资本家,特别是吴荪甫,既把他写成英雄,又以宿命论观点(所谓必然性、神秘力量)把他写成一个失败的英雄。这也是对“五·四”文学“写小人物”传统的背离。写形形色色的资本家,正是跳出“五·四”作家生活和视野的局限,扩大了文学创作的题材。写吴荪甫,既写出了他反动的一面,又写出了他发展民族工业的思想和行动——这是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方面。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成为一个“失败英雄”,获得了读者的同情。这正好证明了这个形象塑造得成功。这又有什么不对呢?三是用“超越”一切的视角写人物,并且以自己的主观认识来选取和剪裁材料,在写作过程中这种主观认识又被“消解在叙述的客观性里”。而这种主观认识又不是“个体的感觉、体验和情绪”(即个人直觉),而是“科学真理”(即马克思主义观点),这又是对“五·四”文学“主观抒情性”这一传统的“背逆”。这又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不是越多样越好吗?是谁规定只准用“主观抒情”这一方式?把主观认识(也就是作家的主体意识)“消解在叙述的客观性里”不正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所要求的吗?包括鲁迅在内的现实主义作家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作家可以写时过境迁的身边琐事,当然也可以及时的反映广阔的社会现象。《子夜》反映现实的“整体性”、“时事性”和“共时性”,不仅是与“五·四”小说的“差别”,而且正是《子夜》的特点,同时又是对“五·四”传统的发展。
总之,“汪文”所说的“五·四”文学传统是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歪曲。而《子夜》、《春蚕》等小说,无论是从思想意义看或是从文学思潮角度看,都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并从而把新文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那么,“汪文”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是不是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柏格森认为人类的认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理性的方式,即用理智去分析现实,从而得到一种概念,并使之清晰化、系统化、理论化,这就把握了整个世界。而这种理性活动总是和功利主义在一起的。一种是个人在具体的、感性的、直接的感受中获得知识,这种感受就是直觉,它是超功利、超概念的。柏格森认为“艺术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心灵的表现”,“美的直觉就象对外界的知觉一样,只能由个人来获得”。所以艺术创作就是个人的直觉过程,艺术家只要向内心自我观照,充分体验自我精神的变化,并表现出自我对世界的看法。如果用理性来指导创作,就象机械论的因果关系一样,只能走向已定的结局。所以他反对艺术家用理智去观察社会生活,要求艺术家把写作的立足点从客观转向主观,从外在的观察转向内心的体验,从寓意的情节表达转向潜意识的非理性的表达。在柏格森看来,艺术作品的优劣,取决于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他个人经历中的体验。请看,“汪文”对所谓“五·四”文学传统的概括和对所谓“茅盾传统”的否定,不就是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具体运用吗?
“失败的艺术品”论。
“徐文(1)”认为《子夜》的结构是极为糟糕的,人物描写(包括吴荪甫在内的所有资本家以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是不成功的,断言《子夜》是“一部失败的艺术品”。理由呢?“徐文(1)”认为“每一个作家都有着体验人生、表现生活的视角。他的经历与体验必须属于他自我的,只有当他从这一属于自我的审美视角出发”,创作才能成功。《蚀》的成功就是因为作家当时“沉缅于个人的迷惘与痛苦中”的情绪与他的审美个性相一致。但是,“让理性的意念去驾驭感性的体验,让政治激情去统领审美的感性冲动,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大通病,也是他们什么素质匮乏的表现。茅盾也不例外”。“徐文(1)”认为茅盾是一个一贯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的作家,在他的内心有“强大而热烈的政治激情”,而1930年间那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激烈论战,诱发他用小说形式来回答托派,表达他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正是这种理性的意念和政治激情,“支(应为‘肢’)解了”他的审美感受,也就是“非审美的政治意识与审美意识的冲突” 导致了《子夜》的失败。论文还强调说这是研究茅盾作品也是研究其他中国作家作品的“逻辑起点”。 “ 徐文(2)”就在这个“逻辑起点”上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见解。
“ 徐文(2)”认为《子夜》的创作,“是主题先行化的产物”。而“主题先行化”的创作原则与创作手法,正是《子夜》模式的首要特征“《子夜》之所以在总体上有重大缺陷,对许多人物的描写缺乏深度”皆因作者在理性意念和政治热情支配下在开笔之前“就已经设置好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主题”。而“主题先行化”必然导致“人物概念化”、“情节斗争化”。这三者就构成了他所谓的“《子夜》模式”。他还把我国四五十年代和新时期出现的一些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看作都是“《子夜》模式”影响下的产品而一概加以贬斥。不仅如此,这位论者还把“文革”期间“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三结合这一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根源说成就在这一“《子夜》模式”。啊!“《子夜》模式”真是罪莫大焉!但必须指出:所谓《子夜》模式,事实上并不存在,而是这位论者所主观编造出来的。
这位论者肯定“让理性去驾驭感性的体验”进行创作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那么,有没有例外呢?他的答复是有的,那就是萨特。他说:“只有萨特才能写出《恶心》那样富有哲理性色彩的小说,比较出色地用小说形式表达出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思想是更“理性的意念”,萨特可以让这样的主题“先行”使创作获得成功,虽然是“极少先的罕例”,也是要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中国作家怎可与他相比呢?
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他的思想体系极为复杂,并且也是发展的。在他的晚年甚至企图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并主张腰围民主而斗争。但就存在主义哲学来说,他的第一原则就是强调人的主观性。他认为人是根据主观性决定自身,使自己成为自己“原意成为的那样”。并且,“只有通过人类现实才有所谓存在”,“由于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才使得各种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这就是说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就是人的意识。他还认为个人自由是由主观决定的,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客观环境总是跟“自我”敌对时,时时威胁着“自我”。萨特的文艺观则正是哲学观的体现。他认为“艺术创作的动机之一,当然是某种感觉上的需要。那就是感觉到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我们是本质的”。他的重要作品之一《恶心》,也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作之一。他力图用小说戏剧等形式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因此,他的作品中往往是哲理性(存在主义哲学观)胜过形象性。我们的论点者彻底否定《子夜》等作品而对萨特及其《恶心》则五体投地,是不是萨特的哲学观和文学观的体现呢?
“社会文件”论。
“蓝文”判定《子夜》不能算是文学作品,而是“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干脆把它从文学领域中剔除出去。理由是:
一是不够“文学水准”。“蓝文”认为《子夜》里“体现伟大主题的章节都是枯燥无味的”,这类章节“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而主线之外却富有魅力的章节“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因此《子夜》的“伟大主题与其艺术魅力,二者表现为一种分离状态”,这就不够“文学水准”了。诚然,《子夜》在艺术上不是没有败笔和缺点,但我不知道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水准是不是可以用加减和算比例等数学方法。
二是“主题先行”。“蓝文”认为“写《子夜》时,党和党的社会科学家已经提出了‘正确’的观点,作家只是把这个 ‘观点’加以‘形象化、通俗化、科学化’”罢了。因此,作品“缺乏思想”。论文还认为《子夜》“追求伟大,但缺乏深刻的思想力量,也未敢触及尖锐的课题”,“追求革命现实主义,但导致了主体性的大大削弱”。众所周知,《子夜》主题是作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当时的社会生活所获得的一种认识,既不是“先行”,更不是别的什么人提供给他的。论文既承认作品有一个“伟大的主题”,又说它“缺乏思想”,岂不是自相矛盾?就当时艺术节激烈论争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回答托派并批判当时城市革命运动中的“左”倾路线,难道不正好“触及时代的尖锐课题”?作家以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政治热情,难道这不正是作品“深刻的思想力量”,不正是作家主体性的体现》?
三是《子夜》“所构造的是一个艺术世界,是作家的虚构,它与现实世界无关,不能对现实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这一论断,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鲁迅早就说过,“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作家所虚构的艺术世界,当然并不就是现实世界,但却是现实世界的反映,怎么能够说它与现实世界无关呢?至于它是否对现实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前面己经谈到,不用重复了。
“蓝文”对《子夜》的评价这样干脆,那么它所依据的理论是什么呢?论文中尽管引用了艾略特、马克·肖莱尔、索绪尔以及布拉格学派的某些论点,但笔者读书不多,还是弄不明白它所依据的是哪一家或者综合各家的学说。单就索绪尔的“符号学”来说,西方学者迄今对其定义和内涵还是众说纷纭,有人甚至认为是“一个可以用来变戏法的名称”。“蓝文”的论述,似乎也与“符号学”无关,也看不出与艾略特、布拉格学派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就其论述的自相矛盾、似是而非来说,只能说是源于论文作者自己的某种偏见。——这可能有些武断了。
上述几种贬低、否定《子夜》、《春蚕》等作品的论文,其理论根据无论是精神分析学说、直觉主义或存在主义(某种偏见除外),其本身可能都包含有合理的成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还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也存在某些共同的或相类似的消极成份,那就是强调个人直觉、主观、感情体验,排斥理性;强调作品只应表现个人的苦闷、颓唐、怀疑、悲观等思想情绪,反对作家自觉地表现明确的社会政治主题。评论者如果片面强调上述各种学书中的消极成份,用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并用来评价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革命现实主义思想作品,那就肯定是格格不入,南辕北辙。
至于“主题先行”说,似乎不是舶来品,而是茅盾首先提出并作了科学解释的。那么上述几位评论家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或明或暗地、或直接或间接地把“主题先行”作为贬低甚至否定《子夜》、《春蚕》等作品的理由之一或主要理由呢?
“蓝文”说“一部作品在动笔之前主题就明确了,但这个主题是生活暗示给作家的”。这一说法不符合创作实际。作家在生活中有了某种感受,觉得对某种社会现象要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就孕育为作品的主题。生活在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作家会写出各种各样主题不同的作品,正是由于作家的个人的经历、观点、感受和见解不同,并不是生活自动“暗示”给作家各种不同的主题。“写作之前主题并不明确,当写作完成之后,作家才明白了作品的主题”。这一情况或许是存在的,比如《雷雨》,发表之后评论者指出它的主题是“暴露大家庭的罪恶”,曹禺说这是他可以“追认”的。不过他也说过在写作之前,他已有“一股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需要发泄。其实这就是他在写作前已孕育的主题,只是在理性上不太明确罢了。有的作品主题极为含蓄和复杂,评论家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甚至经过长期争论也得不到一致看法。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如果说一部作品完成时作家自己对主题是什么“也不明确,永远不明确”,那么这部作品真的是不知所云了。
“主题先行”必然会造成概念化吗?鲁迅的《狂人日记》的主题是他读《通鉴》时想起的,后来一位朋友动员他写稿时才写出来。《阿Q正传》的主题尽管评论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鲁迅自己,要“写出一个现代我们国人的魂灵”——换句话说就是“批判国民性的弱点”这一主题在鲁迅头脑中是蕴酿了好多年,也是应朋友的约稿才写出来的。曹禺写《日出》,是要表现“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一主题,资产阶级的尔虞我诈、纸醉金迷的生活他是熟悉的,但没有“宝和下处”的那种生活,不得不特地去观察、访问、调查,因此甚至引起朋友的误会,但也因此把《日出》写出来了。谁能说这些作品是概念化的呢?左拉在1868年就决定要描绘一幅“充满疯狂而耻辱的奇异时代的图画”,从而表现法国“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及社会史”这样一个主题的长达20卷而又各自独立、总题为《鲁贡·马卡尔》的长篇小说,第一卷在3年后出版,最后一卷写成出版已是20多年以后(1893)。这可说是典型的“主题先行”了,但有谁能够说它是概念化的、失败的作品?至于小说中所包含的思想是否正确那是另一回事。
至于《子夜》、《春蚕》等作品的主题与作家生活体验的关系,茅盾自己和一些评论者已作了充分的说明和论证,这里不重复。上述几位论者在用西方的几种理论观点来贬低和否定《子夜》等作品时为什么又都一致用了“主题先行”说呢?其实他们批判“主题先行”只是幌子,真正用意是不赞成作家自觉地以社会科学理论(即指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明确地表现社会政治性的主题,正是和他们强调创作只应凭作家个人的直觉、主观,排斥理性,创作也只要表现个人的直觉、个人的感情体验等主张相一致的。他们的真正用意也就在此,是无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