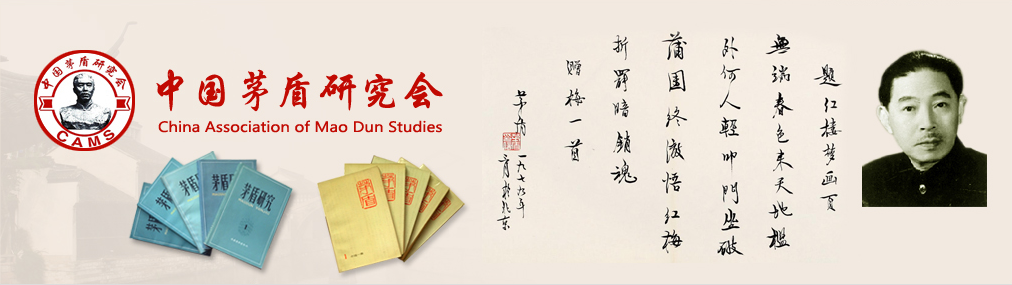乌镇行
赵冬梅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3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渔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入;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陶渊明《桃花源记》
在雨下得愈来愈紧的安渡坊码头排队登上渡船,慢慢摇离乌镇西栅景区,回望掩映在烟雨树丛中的石桥与黑瓦白墙木门窗的房舍,竟突然想起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只是此一时非彼一时矣。
初四下午五点多,我们乘旅游巴士到达乌镇,远远望见作为镇标的古墙,还未来得及发思古之幽情,便遇堵车,子夜路上走走停停、不见首尾的车流,仿佛回到了北京高峰时段令人气闷的环路。从车窗望出去,是所有旅游区的常见景象,应运而生的林立商铺,密密停放的挂着各地车牌的私家车,一眼便知是游人的二三行人,一红一白镶蓝边的竖长条幅“乌镇国际旅游区”和“品位国际风情小城/徜徉江南千年古镇”,挂在黑色仿古路灯杆的两侧。
由于行前未做功课,直到这时才知道,作为旅游区的乌镇,并不是一个可以驱车随意进入的城镇,而是在市河两边,分别隔离出了东栅、西栅两个各售门票的景区;作为城镇的乌镇,作为乌镇人的乌镇,从地图上看,则由这两个景区之外的几条主要街道组成,虽然仍有大小河流交插其间(据说有南栅、北栅尚未开发出来),不过一路走马观花看来,未见枕水人家,和中国大地上尤其是江浙地区的其他现代小城,并无太大差别。我们要入住的酒店在西栅,这意味着我们的游览范围也在此,若想去茅盾先生故居所在的东栅,需出西栅,乘坐景区间的免费班车或步行(原以为乘木船——水乡古镇主要的交通工具——便可由西栅到东栅),通过跨越市河的乌镇大桥,沿子夜路回到镇标附近的东栅景区入口,另购票进入。
卡尔维诺(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城市与眼睛之二”中写到,是观看者的心情,你吹着口哨昂首而行或你指甲掐着手心低头走路,“赋予珍茹德这座城市形状”。所以,当我们在夜色中由步行栈道进入西栅,尽管脚下已是青石板路,身旁已是典型的水乡建筑,不远的河边也已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光,但出乎意料的游人之多之拥挤,恍若置身于北京的地坛庙会或前门大栅栏,令人茫然又倦怠,当时便打消了第二天自行去东栅的念头。而当我们吃过晚饭,重整精神,冒着时断时续的毛毛细雨,试探着由一条幽暗的小弄步入西栅大街,却又如武陵渔人,立刻豁然开朗。
正是春节,位于西市河北岸的整条西栅大街上,悬挂着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花灯,是装饰也做照明,因着彩纸、图案的过滤,光线既朦胧又有着乡俗的喜庆,加之不时有游人手提花灯走过,年的气氛扑面而来。虽叫做大街,其实是古朴狭窄的石板路,路两旁二三层高的房屋可声气相闻,每行一段便有一座石桥通往对岸,等走过对岸那些一面临水、由大小石桥连接且颇显曲折的秀水廊街、女红街、通安街后,才晓得这就是西栅的大街了,它还算宽,因此有一长段的路中央一字摆着许多木方桌和条凳,为人们聚餐所用,可以想象出那份热气腾腾的场景;有了花灯,它也算是亮的,其余无论是游人密集的女红街,还是幽僻的小弄,几乎都要靠店铺中透出的昏黄灯光来照明,连河中的游船上,也只挂了一盏影影绰绰的灯泡。都讲乌镇(其实就是西栅啦,东栅晚上并不开放)的夜景漂亮,除去灯光因依水流而显迤逦,岸上、水中交相呼应,以及水乡特色的房屋、石桥的映衬外,灯光的昏暗也是重要的原因,如果到处是闪烁的霓虹灯,亮如白昼的射灯,想来在这飘着雨的深夜,不会有这么多的人仍流连在石板街上不愿离去。
或许和灯光的昏暗有关,西栅的夜晚显得特别静,尽管游人熙熙攘攘,但所有的声音,好像都被雨打湿的夜幕、被古老的房屋、被桥下幽幽的河水“吸收”了,留下的,是如默片一样的一个一个画面,也是人们为了珍藏而拍下的一张一张照片。
第二天为了避开人流,早早出了门,天上仍飘着若有若无的小雨,湿漉漉的石板路、石桥,石桥下的流水,都和空气一样清冽干净,西栅大街上的花灯,此时也分外明艳。店铺还未开门,零星的行人,偶尔划过的载货的木船,整个西栅寂寥、幽长、空旷,正好可以不受干扰地随意而行。稠丽的夜色退去,所有的景物皆露出它本来的面目,高耸的风火墙,紧闭的木门,推开或支起的木窗,屋顶的瓦片,脚下的石板,水边的回廊,都已斑斑驳驳,是风雨、岁月侵蚀的痕迹,所谓的古意、人们所怀的“旧”,便是如此吧。由于是阴雨天,河两岸的垂柳也尚未染绿,站在石桥上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西栅,都可称得上是一幅浓淡相异、布局合理、浑然天成的水墨画,是令无数人魂牵梦萦的烟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
就这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如在画中漫步时,不知不觉雨愈下愈密,游人也像潮水一样涌入了大街小巷,仓皇中才突然醒悟,这里是景区!而昨晚的西栅之所以觉得漂亮、安静,最关键的也因它是景区,是以保留完整、原汁原味的水乡古镇而著称的景区,所以这里不会有聒噪的汽车喇叭声、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当然也就不会有由鸡犬声、爆油锅声、笑闹声、啼哭声、争吵声等汇合而成的居家过日子的嘈杂声;即使是那些极现代的酒吧、咖啡厅、SPA馆,由于都设置在过去的民居、会所中,也没有那些夸张、花哨的招牌,外面看来,与古镇整体的风貌并不相悖;尤其是邻河的窗口或凉台上,多挂着腊鱼、腊肉、腊肠,给人一种富足的人间烟火的气息,使人不由对那敞开的窗口浮想联翩;也因管理得当,游人再多,这里的任何一个角落,也见不到景区常见的随处乱丢的垃圾。所有这一切,便给人营造了一个身临其境、沉浸其中的“纯粹”的水乡生活的氛围。
只是当你想到,这里所有的民居,都已是商铺、民宿客栈,所有兴致高昂、不知疲倦的行人,都是过客,不禁会怅然若失。
它自然已不是那个有着一千多年建镇史的“真实”的乌镇了,也不是茅盾先生曾经生活过、描写过的乌镇了,如广告中所宣传的,它是一个世界遗产级的休闲度假景区(指西栅)、一个水乡古镇风情观光景区(指东栅)。因此,它既是一个消费对象,也是一个文化符号;是麦尔(Meyer)在《天安门之龙》中所谈到的,它“首先是一个观念,然后才是一个城市”,这个观念“赋予这一城市及其环境以形式和内容”;是人们带着各自先验的印象——或得自茅盾先生的文字,得自乌将军、昭明太子、瘟都元帅等某段历史传说,得自高竿船、蓝印花布、三白酒等某个民间风物习俗,或得自黄磊、刘若英主演的《似水年华》及其他影视剧,或仅仅得自某幅画、某张照片——来印证、凭吊的地方;所以,它还是一个历史、记忆、文化、想像的混合体,当然,这个“混合体”的形成有赖于每个人的阅历,比如对于不满六岁的宋映都小朋友而言,如果没有造型别致的棒棒糖(“我没吃过这种棒棒糖”)和花灯(“幼儿园过春节时也挂灯笼”),没有童玩宝铺和精致的手工铁皮汽车模型(“我没有这样的小汽车”),乌镇就是一个有好多“旧房子”的地方。
同时,它也体现了古城古镇(文物古迹/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化城镇建设之间的辨证关系。来乌镇的途中,曾在高速公路上看到指向“柯桥”的路标,当时便想起了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和小说中的另一个实名小镇“华舍”。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透过小女孩秧宝宝的眼睛,呈现了这两个江南古镇的面貌——水乡古镇华舍,“依着生活的需要”,一点一点增减、改建、加固,临水的房屋、沿水的街市、河道窄处的一领桥、河道宽处的鸭棚、断头河处的“上种红菱下种藕”,都有着惊人的合理,达到了谐和平衡的美,“体现了对生活和人深刻的理解”,然而,如此和谐的小镇,却被垃圾和泥石流般的水泥“挤歪了形状,半埋半露”,河道里的水,人们也早已不再使用;柯桥虽是一个比华舍大的古镇,但却“像个中型城市”,以往的水道填平了大半,变成北方城市那样宽展的街道,往昔的船只换成车水马龙,老街“快给新街挤没了,剩下那么掐头去尾的一截,几领桥,供绍兴,杭州的旅行团来观光”,而为了造出一种烟花亭台的江南韵致,新修了有着柳丝与美人靠的长廊、水道、粉墙,但周遭环境的粗糙、水的浑和臭、人的杂沓、遍地的垃圾、大街上喧嚣的车流,使得这台风景是“扎眼的新和亮,反露出俗艳”。
尽管你会为乌镇的景区化而若有所失;尽管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言,人们越来越注重环境建设的“面向他者”的象征意义,许多旅游区推出的“最真实”的地方,只是把当地的风俗进行了“再创造”,从而“卖给”游客一个“正宗”的地方形象,文化的多样性成了大众旅游业的一个地方色彩的“供应商”,但比起华舍的老街被新街“挤歪了形状”,柯桥的不新不旧、粗糙俗艳,和它们被污染的河水、遍地的垃圾,乌镇西栅与东栅的被作为景区隔离保护,并营造出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水乡古镇的氛围,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也许,在一个快速城市化,在一个经济至上的消费时代,古城古镇或文物古迹、传统民间文化,只能以“文化品牌”,或民俗旅游中的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方能得以保存、流传。
当你厌倦了万丈红尘(或万丈雾霾)、刻板重复的都市生活,你且耐下心经过堵车,以步行或摆渡的方式进入西栅,它就是一个令你惊艳、可容你暂时生活在别处的“桃花源”;但它绝不会“不复得路”,而这也正是让人担忧的地方,它是否会因过度开发、过度商业化、过度消费,而丧失它的“纯粹”,“遂无问津者”?
那天上午,被人潮打乱了游逛的脚步,谁知竟误入灵水居,在一片僻静的、犹有着翠竹绿叶和腊梅余香的园林中,偶遇茅盾纪念堂与茅盾陵园,算是弥补了未去东栅的遗憾;后在一座临水的咖啡吧休息,浏览墙上的老照片时,竟又看到茅盾先生晚年的一张合影,这张黑白照片所弥漫出的和谐温煦之感,让人直觉是与家中至亲晚辈的合影,在三位年龄不同但看上去都很美的女性的右后边,同样蹲着的微微笑着的老人的脸,如此的安逸慈祥,虽沧桑却风清云淡、岁月静好,令人肃然感动。这两次偶遇,如同此次的乌镇之行,有意外,便有喜悦,并留下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