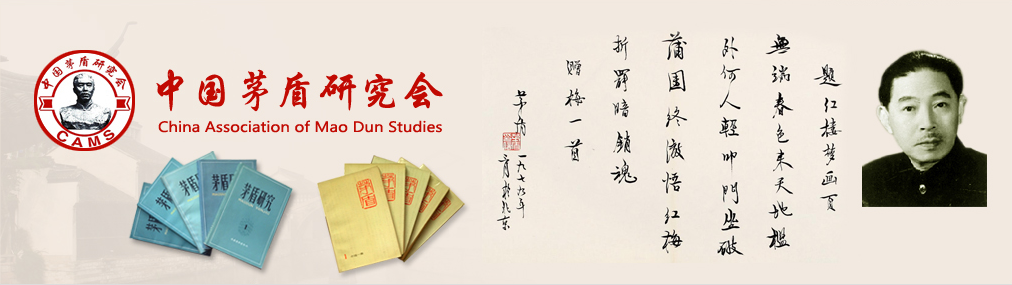乌镇行
李明
浙江桐乡乌镇,是一代文豪茅盾的故乡,也是浓缩了中国江南小镇之美的水乡,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称,我心仪已久,此次与友人结伴出游,可谓又圆了自己一个小小的梦。
车进桐乡,看到有“茅盾路”,友人开玩笑说:这条路名字取得好,让人不知道往哪开。但还是很快就到了乌镇。镇中有一条河,过了河,到了观前街“茅盾故居”前。我还没有进入旅游状态,只是感觉人多得不得了。一眼望去,那狭小的街道上密麻麻人头攒动,你来我往,摩肩接踵,人气旺盛。幸好修真观前有一处空地,我站在那里,抬头看“桐乡花鼓”戏台,感受眼中江南小镇的古朴建筑风貌,仿佛置身于遥远的历史场景中。
临河二楼一家饭馆用餐。倚在窗口,见乌篷船轻轻驶过,河边的木屋,木屋前的青石板,惹人疼爱的小桥,垂挂的字号招幌,河边洗衣人……我脑中便不由得想起“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的话,感觉坐在这样的地方,不来两杯,定会缺少某种闲情雅趣,或者说是艺术的韵致吧。
地灵人杰。便来到茅盾小时候读书的立志书院。人流熙熙的环境中,再美妙的楹联也无心观赏。一尊白玉石像,后有周巍峙题的金色字迹:文学巨匠茅盾。闪光灯频频闪烁。一孩子问母亲“巨匠”是什么意思。母亲只说是大文学家,我看孩子还是愣在那。其实我也是不大喜欢“巨匠”这个词的,挂个“一代文豪茅盾”不也挺好。“巨匠”自然是伟大的称赞,但总抹不去我从小对“匠”和“匠气十足”的记忆与偏见。我们这个时代是好大喜功的,我总感觉爱故弄玄虚,或者贪图虚饰夸张。巨人、大师、大家、大学、大餐、什么什么城……遍地都是,但就是给人某种名不副实的错觉或幻觉。茅盾自然是伟大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深信。但伟大是不需要夸张的,这也正是我所理解的“伟大”的本质所在。
于是被人流裹挟着来到了“钱币纪念馆”,的确再一次感受了马克思的吃饭哲学。总是沉醉于文化活动,蓦然发现,经济活动才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著。那么多钱币,斑斑锈迹展示着历史的陈迹,游客惊叹着,拍照着。在一个“铜臭”从我们的生活字典里消失的时代,“钱庄”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
“江南历代卧具展览馆”的确值得人多流连一会。今天的大都市人,“卧”是很奢侈的,除非不得不“卧”或“病卧”,连“醉卧”也是极为少见的。上海、北京的地铁里,满眼都是在椅子上、甚至抓着扶手打瞌睡的人。那一刻,我为自己是现代都市人感到难过。睡觉是人最基本的权利,都市人一天都说自己忙疯了,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那究竟要干吗?我们的古人对睡觉是很讲究的,那些我们今天动辄几百万捣腾来捣腾去的“古董卧具”,也就是前人睡觉的床。各式各样,雕栏画栋,悦人耳目,静人心思。在此中逗留,颇觉时光的凝滞,悠然的美妙,睡觉的舒服。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是我们古人很重要的生活观念。现在的人可有点走偏了,酒店吃饭也要穿插艺术品拍卖,故意裸露个把砖头,挂上几串辣椒,悬上几株玉米棒,饭桌边置上古董橱窗,不伦不类,把审美生活日常化了,其实一点也不美,一点也不生活。
染坊是很有味道的。躲在若垂天之云的花布后头,露出半张脸来,咯嚓,游客们写下了自己的诗句。染印工艺是复杂的,导游滔滔不绝说得越多,游客脸上无知的表情越厚重。一种历史的记忆,岂是匆匆走马观花所能感受?但那深蓝而洒满碎花的花布,相信能给人留下生命的色彩。
乌镇有名的“三白酒”,免费品尝。古旧的方桌、条凳,一字儿排开的酒坛,令我想起“水村山郭酒旗风”、“若问酒家何处有”等古诗句来。唉,唉,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是风景独特的地方,脑中就只有前人的诗句。比如到杭州,再怎么想“创造”,还是觉得“接天莲叶无穷碧”和“淡妆浓抹总相宜”等古人诗句已经将其美道尽了;见黄河,总是“黄河远上白云间”、“白日依山尽”等句,搜肠刮肚,也没有更好的抒发胸臆的句子。人之一生,随着年龄的增长,由蔑古到学古、尊古、疑古、信古、释古、厚古、崇古、泥古,种种选择,都有个历史意识在里边。没有了过去的历史,我们今人的美好生活也将会大打折扣。汲取古人智慧,反思西人竞争,审视现实人生,开创美好生活,也许是我接下来要走的路吧。我厚着脸,连饮三杯“三白酒”,倒感觉周围顿时多了点诗意。
诗意其实无所不在,只要我能把脚下的路走好,以诗的眼光去看周围。的确太美了,这乌镇河边的景色。深巷幽幽,古木散淡,垂柳婆娑,水光潋滟,长廊迂迴,烟霭迷濛……就算我再寻出多少形容的字汇,也是无法描述其美的。更何况我一向拙于风景的描写,笔力不佳。那时便羡慕河边的画家,他能用画笔涂抹出自然的美丽。一切景语皆情语,是的。我心里荡漾着宁静和幸福,我希望天下有更多的人来领略和欣赏这江南小镇的景致,他们的感受,一定会非常丰富。
夜饭后,我们漫步深巷。夜晚的乌镇笼上了妙曼而神秘的面纱,我更感觉置身画中。很静,光影里几个游客的身影。昭明书院的书香气息很浓,美丽的姑娘告诉我们:九点半以前均可来此看书。我想,到了这里,我也只看古书。
白莲塔矗在不远处,流光溢彩,塔影倒映河水中,也就成了自己心中的海市蜃楼。一切是那么幽静,朦胧,迷离戃恍……我便溶入这乌镇的夜色中了。
翌日,来到茅盾先生塑像前,摊开的黑色大理石金字的《夕阳》(《子夜》初名),在朝暾的映照下格外引人注目。伟大的文学创造者啊,您凝视着远方,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的创造更伟大,是的,这是您说的话,也将如您一样,镌刻在不朽的人类的记忆中。
我有幸听到了您生前的声音。您的江浙普通话不是很难听懂,我连听带猜明白了您在解释“茅盾”笔名的由来;您说话的语速很慢,甚至让人感觉上句不接下句,中间等待很长。哦,您可能是七八十岁上说那些话的。我听着,心里深深敬佩着您语词的准确,记录下来就是文章。哦,您的文章正如您的说话,细腻而严密。您说您一生秉承慈训,谨言慎行。的确,您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严谨。您下笔总很谨慎,您写小说总打提纲,这使得许多人以为您理性过强,削弱了您作品的艺术价值。其实,这是对您的误解。您的确是不大轻易动感情的人,但您一动,就是真情。这是那些没有全部细读您作品的人可能还没有感受到的。我想在这里摘录您文章里的一小段,同大家一道品味:
在进立志小学的第二年夏天,父亲去世了。母亲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我和弟弟身上。尤其对我,因为我是长子,管教极严,听得下课铃声而我还没回家,一定要查问我为什么迟到,是不是到别处去玩了。有一天,教算学的先生病了,我急要回家,可是一个年纪比我大五、六岁的同学拉着我跟他玩,我不肯,他在后面追,自己不小心在学校大院子里一棵桂树旁边跌了一跤,膝头和手腕的皮肤的表层擦破了,手腕上还出了点血。这个同学拉着我到我家中向母亲告状。母亲安慰那个同学,又给他几十个制钱,说是医治他那个早已血止的手腕。这时,我的祖母和最会挑剔的二姑母(因他排行是第二)都在场,二姑母还说了几句讽刺母亲的话,于是母亲突然大怒,拉我上楼,关了房门,拿起从前家塾中的硬木大戒尺,便要打我。过去,母亲也打我,不过用裁衣的竹尺打手心,轻轻几下而已。如今举起这硬木的大戒尺,我怕极了,快步开了房门,直往楼下跑,还听得母亲在房门边恨声说:“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儿子了。”我一直跑出大门到街上去了。祖母令三叔找我。三叔找不到,回家复命。祖母更着急了,却又不便埋怨我母亲。我在街上走了一会儿,觉得还是应当回学校请沈听蕉先生替我说情。沈先生是看见那个同学自己绊了一跤的。沈先生带我到家中大门内那个小院子里,请母亲出来说话。母亲却不下楼,就在楼上面临院子的窗口听沈先生说明。沈先生说:“这事我当场看见。是那孩子不好,他要追德鸿,自己绊了跤,反诬告德鸿。怕你不信,我来作证。”又说:“大嫂读书知礼,岂不闻孝子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乎?德鸿做得对。”母亲听了,默然片刻,只说了“谢谢沈先生”就回房去了。祖母不懂沈先生那两句文言,看见母亲只说“谢谢”就回房,以为母亲仍要打我,带我到房中。这时母亲背窗而坐,祖母叫我跪在母亲膝前,我也哭着说:“妈妈,打吧。”母亲泪如雨下,只说了“你的父亲若在,不用我……”就说不下去,拉我起来。[1]
真情永远是伟大文学的质素。
您是我所景仰的伟大的文学家。
别了,乌镇;别了,文豪的故乡;别了,我喜爱的“三白”酒!有机会,我还会再来。那时,我对乌镇和茅盾先生的理解,也许会更深入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