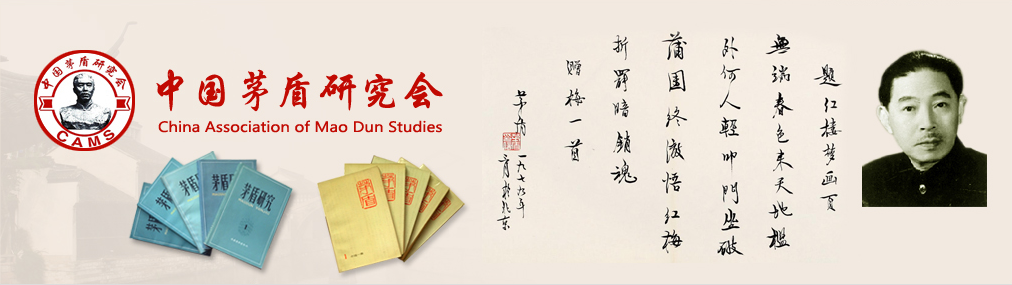品味乌镇
钟桂松
品味乌镇,一股氤氲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仿佛让人置身于历史与现实交错的时空里,每个人都在想像着过去发生过或没有发生过的往事,历史时空的交错,成为驰骋千年的思绪风帆,成为每个到乌镇的人的心里的一道风景,现实洒落在淡淡的斜阳余辉里,褐色的石板路,石帮岸以及帮岸上廊棚,带排门的店铺,错落无序然而实则有序的青瓦面,由于岁月的关照,变成黑色深褐色,沐浴在金色阳光里的现实,也脱不去历史的气息,光是新鲜的,现实的,透出来的气息是历史的。无论你想到还是没有想到或不愿想到,历史永远和现实联在一起,无法改变。因些,在扑面而来的带着水乡特有气味的历史气息环绕周身的同时,心灵也被这中国乌镇的历史所震撼。
一代一代的延续传承,构成历史和现实无法抗拒的景观,人类也如些,和人类紧密相联的居住地亦如些。中国地大物博,想想西部沙漠里曾经有过的辉煌,当年金戈铁马,市廛繁华的驿站,草繁马肥的村落,倏忽间消失在历史和黄沙的广袤里,这是历史的残酷也是历史的规律,善待历史,就是善待现实。沿海地区的一些在上个世纪下半叶新建的市镇,虽然至今尚未有一棵上百年历史的大树, 但也仍在创造着历史,为了遥远的将来创造和积聚着历史的每一个元素。乌镇历史上的先人们,也不都这样过来的么?我们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干脆说,我们站在某个河埠石阶上,站在某一座小石桥上,或者走进某一条小街,再张望一下某一条幽深的长长的弄堂,无数的历史思绪就会潮水般地涌来。想象着这一块亿万年前由大海变成的冲积平原,一马平川。后来是杂树杂草遍地,再后来是先民以吃螃蟹的精神,寻觅到这一方土地,开沟排水渐渐变成一条河,变成多条河。繁衍生息的先民们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同胞,也以勤劳和智慧创造着今天称为乌镇的历史,渐渐地有了乌墩青墩之说。名称,本来是人类交流需要的产物,所以打开乌镇历史这本书,姓氏多元聚集的事实,足以证明乌镇开放由来已久。宋朝南迁之后,乌镇的经济发展吸引了不少精英人物,之后也产生了不少历史精英,达官贵人也好,文人墨客也罢,都是往经济富庶的地方去的,反过来又影响了这些历史——只不过这些影响并非立竿见影罢了。长期的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便是最好的领会。至于后来所谓的两省三府七县交界地,那是统治者为管理需要而人为设置的一种噱头而已。至今仍广为传诵的乌镇前贤,可谓群星灿烂。南朝文学家沈约、南宋吏部侍郎陈与义、以机智和才情而被称为“真君子”和乌镇徐文长的明朝人李乐、明未清初的农学家张履祥,以及近代和现代更多的人物,同在一条历史链上建功,同在一座镇上立业,真让人对这些同一地域出生的先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乌镇的繁华,乌镇的灵秀,乌镇的深沉,全是乌镇历史使然。东西南北各长七华里的市镇,在杭嘉湖平原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小街上的每一块踩得凹下去的石板,都可以向每一位曾经走过或没有到过乌镇的人诉说历史的往事。我曾听一位北方来的学者说过,在乌镇,每一脚都踩在历史上。因此,在乌镇,看到的是历史,踩到的也是历史,所以得轻轻地走,静静地看。喧闹并不是乌镇的常态,而静谧才是乌镇的本性!清晨,乌镇的薄雾,似蝉衣似纱笼,朦朦胧胧的现实意境,将整个水乡古镇变成人间仙境,让人呼吸着湿润空气的同时感到一种沁人心脾的美。倘是春天的早晨,乡村的美和气息也随着晨风飘到镇上,弥漫到镇上角角落落。然而从清晨的薄雾里,隐隐约约能体味到乌镇的往昔。延续了千百年的茶馆里,依然人声鼎沸,满口的乌镇本地方言透出融融的乡情;河埠上提水洗衣的身影在晨曦里随着乌镇的历史晃动了千百年,依然那么矫健和朦胧;小街上的人流仿佛走不尽流不完似的,一批一批,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街坊乡邻都在小街上来来往往,早晨走来,走过黄昏,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更像黄昏,黄昏是从早晨走来的,品味过去,灯火阑珊,先民们的智慧,先民们的物质遗存构成了今日的中国乌镇,构成了今日中国的乌镇世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又是从今天开始的,太阳又从水乡晨曦中升起。
阳光是软软的,气温是适中的,水光潋滟,和风细雨,垂柳下碧水一泓,桃花开处蝶来蜂往。恬静的乌镇有着不算独特却不一般的文化。
阳光的充足和雨水的充沛带来湿润的气候,乌镇四乡变得丰衣足食——蚕桑半年稻,穿有丝绸,吃有白米。因此在乌镇历史上因四乡饥饿而发生的血案相对于其它地方少多了!故有人说,乌镇这个地方自开发之后历朝历代少将军而多文人,这实在是地理自然环境影响的结果。深层次的探究,是地域文化造成的人的性格取向。在年日照时数为2000多小时的地方,给人的心理上的影响是温暖的、安全的。在万物生长靠太阳的自然经济时代里,这2000多小时的日照力量巨大,无以伦比,影响着方方面面,慢慢地在性格里亦悄无声息地滋长出一种温和的精神追求!所以乌镇这个地方,历史上民风优雅,重学尚文。而学校多文人多成为这个水乡古镇的一道独特风景。
据记载,乌镇的文化教育在南宋时已甲于一邑。明创学社,清建书院、义学、私塾等,林林总总,绵延不绝。到抗战前,多元办学在乌镇仍蔚然成风,据说官办的、私办的、商团办的、教会办的各类小学达十所。这在一个近万人的小镇上,可谓十分繁荣了。正因为如此,科举时代的乌镇,自宋至清,考取进士64人,举人167人。也正因有这样的底蕴,乌镇与宁波等地不同,从古至今没有产生过大商人,在国内称得上商界巨擘的,只能出在宁波。而乌镇,只能出文坛巨匠。看来,地域文化造成的这种特征和差异也是一种规律,不可更变。
重学尚文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人际关系上,君子风度便是其中一例。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滩的两大文学团体——鸳鸯蝴蝶派和文学研究会之间的争论,是乎稍具文化常识的人皆知晓。说来也巧,这两大文学阵营的主要骨干严独鹤和沈雁冰,都是乌镇人。只不过严独鹤年长些而沈雁冰年轻些。但翻遍沈雁冰的争论文章,尖锐者有之,锋利人者有之,竟没有一句是针对老乡的。而严独鹤也没有半句指责年轻沈雁冰的。文学理念不同,但决不用诟骂或激烈方式来攻击对方,这就是乌镇典型的一种性格。在乌镇性格的另一面则是非常地平民化。走进乌镇所有高屋大厅,风格上并没有威严的居高临下的气势,宽敞的大厅里除了文化的亲和力,还有一种节奏并不快的韵律回旋在乌镇这些有钱人家的高厅大屋内,一副谦谦君子的风度。百姓民居建筑结构也反映出百姓性格的大概,沿街民居,大都是下面店堂楼上住房的格局,店堂里的曲尺柜成为居民营生的地方,在市场文化中塑造了一种平和的心理模型。
乌镇平和的性格里,也蕴含着勤快和智慧。历来,在春天的脚步里,四乡农民穿梭般进镇还乡,寻找各种商机乃至没有商机创造商机,这是这一季节聪明才智的集中体现。譬如举办各类的“会”,各类的“节”。而这些会和节的策划,一部分是传说的,世代相袭;一部分是创新的,吸引每年这个时期的农民,拉动商业。这着实是一种聪明,一种不伤任何东西且多赢的聪明。所以,乌镇平和个时期的性格里,春天发生的一切是勤快和智慧的最好注脚。温和湿润的气候,充足的阳光,滋养了大地万物,也孕育了某种特点的文化性格。假如长年缺少雨水的地方的文化性格,决不会如此平和。居住在深山岙里长年缺少阳光的地方的也会和阳光充足的地方大相径庭。所以站在乌镇的河边,坐在茶馆里喝茶,同时望着河里南来北往的船只,思绪会纵横万里,驰骋千年。寻觅着这个千年古镇的文化性格,欣赏着这个文化性格积淀下来的小桥、民居、河流,以及塑造这种文化性格的阳光和雨水。 乌镇的园林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从历史眼光来审视或者欣赏这些园林,很可说明这一带地方的经济发展有它自身的物点和规律从文化视角看,乌镇的园林虽无苏州的豪华,却保持了空灵的风格。而且在空灵中讲究实用,审美上的愉悦和生活中的实用兼而有之。驻足历史的园林门槛上,凝望这些园林的往事,让人感慨。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光阴难追,翻天覆地。大江东去的历史感叹,常常从一堆假山石里,从一棵历经午年百年的大树后,从一段残垣中不经意的透出来,传达给21世纪的现代人。
园林有公园和私园之分,在乌镇上千年的历史上,私家园林要居多,这些私家园林也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当官的有了钱之后,回乡修个园林。一来装装派头,二来可以颐养天年。第二类是经商下海的人有了积蓄之后,也附庸风雅,延请名师,打造名园。细细琢磨其实还有一个作用,经商发财之后造个园林不仅装点门面,而且可以在园里某某亭洽谈生意,一边展示自己家底殷实,一边欣赏园林四时不同的景色。这样的生意洽谈,估计成功率很高。所以,旧小说里常有去亭子里谈事的情节,旧戏里也常常有接待来客里手一伸,道声“请”。平心而论,当年乌镇这些园林并不全是商业气,而是极富文化意味的。光是历朝历代园林的名称,如竹素园、琪园、蠡勺园、宜园、半亩园、颐园、庸园、适园等,就并不仅仅作为符号,还寄寓着主人的情趣爱好,表达出主人的志向或许还蕴含了主人不便向外人道的隐情。可惜,在今天的残阳里,我们已看不到这些旧时园林的风采,偶尔有一砖半瓦埋没在荒草之中,一块条石半露在黑土之外,让人一阵惊喜。然而仔细一听,在这些断墙遗址里,似乎有呻吟,又似乎有歌唱。这些没有生命却有感情的旧时遗物,在悲叹世事沧桑的同时又显示出历史的辉煌。当年园林落成时宾客如云,三五知已在园中品茗吟诗,儿童绕着假山嘻闹……如今都化成了碎瓦片和断石条。当然这记忆里也包括一把熊熊大火吞噬园内一切,一场兵荒马乱墙倒门破的镜头。 对历史的钟爱也就是对当下的热爱,如今乌镇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画面源于时人对历史的崇敬和热爱。再现也好,重现也罢,每一处景点里,都凝聚着时人的聪明才智和心血,但同时也是对乌镇历史遗存的继承和开掘,让人们有机会聆听历史的诉说!
园林的遗存是乌镇最具古趣的。在乌镇这样古老的市镇里,随意徜徉,或许在不经意间就踩在某个古时乌镇园林的遗存上。或能拾起上古时儿童剩下来的半句歌声,或能从半垛残墙的青苔上觅得一鳞半爪的记忆。一块界碑几百年间注视着千千万万来往的各色人等,各路人马。假如它是一个能说话的老人,可以向你诉说在它眼前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历史就是由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在过去的故事写就的。所以善待现实就是善待历史。
新时代的旋律在历史的往事上响起,走在乌镇这座千年古镇的历史大道上,让人感到时人的任重和道远。后人已不再满足独家享受的私家园林式的遗存,而要求有亲民思想和营造全民都能享受的公共空间。同样的缘由,后人将来凝视今天,若能够不用异样的目光来审视,而用自豪的神情来赞扬这段过程,作为今人才会有今世无憾之感。“文化”这个词在汉语里太伟大了,它能囊括所有人的记忆,也囊括人们的所有行为,同样也囊括所有物质的载体。北方的皇家园林是帝王文化,面南方的私家园林则是世俗文化,漫步乌镇的历史园林,思绪飞动在历史的时空里,让人神游也让人神往! 走进乌镇长长的石板小街,一道晨光和斜阳静静地泻在条石上,洒在排门上,洒在只有一步之高的石台阶上,让人感到温馨和宁静,谁也不愿去踩碎这和谐。置身在这样的小街,无论是风是晴还是阴,总是让人有种着落感,有种无法抗拒的亲和力!仿佛是站在磁场里,思绪无法脱身。人生从幼年到晚年,只是倏忽之间,千年沧桑似乎从小街那头走来。
这个由众多小街、小河、小桥构成基本构架的古镇,鸟瞰起来,十分壮观。十字形的格局,连街带河一并展现,清朗得有点道骨风范。在乌镇历史上,街巷众多,万历间有7坊58巷,康熙年间有8坊67巷,乾隆年间有8坊68巷,而今只剩39条巷弄了。自然,经济繁荣与否与巷弄小街多少并无直接联系,但与人们心情却有割不断的联系。嘻笑无忌的儿童赤着膊在小街里奔来跑去的情景,让中年以上的人们羡慕不已。而躺在一张小桥边的竹椅上,摇着蒲扇乘凉看月亮的惬意,是躲在空调房里一个夏天不出一滴汗的时人所无法体会到的。小街上远远飘来的油炸臭豆腐干的香味,迟迟不肯散去,一直从小街的一头香到另一头,从上午香到下午,无论进镇的农民还是镇上的孩子莫不被它所引诱,垂涎三尺!小镇的风情有时是在气味里。
然而最具人文色彩的莫过于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们穿行于人生之路,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共同走过这个小街演绎着人生的活剧。而这活剧主要在这些来来往往的凡夫俗子心里演出,悲剧、喜剧、正剧或者悲喜剧,倘若去每个行人的心里作一番旅行,可以演绎出许多精彩动人的故事。曾几何时,一出《林家铺子》,算得上精明能干的林老板站在自家的店铺的宅区人家,揣摩人家心里,兜售着自己的存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街是人生旅途,小街也是人生舞台,在充满历史意义的中国乌镇小街上,每一块石板在承受人们踩踏的同时,记住了古往今来的历史。无论兵荒马乱,无论欢呼雀跃,都曾成群结队地走在这长长的小街上,记录着历史带来的悲壮和欢乐!
乌镇的小街是名副其实的,首先是街的事实。所有被称为街的,都是因为两边有店铺的缘故。而乌镇的街临河而修,而且因为有河,两边店铺也有区别。靠河边的店铺称[下岸],对面的店铺在乌镇却没有称[上岸]的习惯。这就是水乡古镇带来的文化,带来的特色。其次是小街真小,乌镇南栅、北栅、西栅及市中心的每一条老街都很小,小到宽不到盈丈,一副馄饨担换个肩挑都困难;小到邻居晒衣裳竹竿搭在对面邻居的窗台上,走在街上,常常被刚晾出来的衣裳水淋着,躲得了这一次,躲不了那一次。所以过去走在乌镇小街上,不少人常常眼朝上看,昂着头走路,主要是防备被晾在上面的湿衣服淋着。乌镇的小街还有个特点,就是长,一个小小的乌镇,人口不过万人,但街的长度在杭嘉湖乃于江南小镇中算个奇迹,东西南北都是各长七华里!
街是乌镇的小,街是乌镇的长,韵味也是乌镇的足。感觉走在这样的小街上,听着各种不算大声的吆喝声,闻着店铺飘出来的诱人香味,熙熙攘攘把你挤进各种店铺,不买东西看看地方风物上特产也是一种享受,也算一种消费。惟有如此,仿佛才像进乌镇,才品味到、感受到乌镇的韵味。
没有人能够想像,假如乌镇没有河,那乌镇是什么模样?假如乌镇仅仅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河,又会是怎样的模样?所以,河,在乌镇,是血脉,是生命,是文化也是乌镇的性格!我们不用去翻乌镇的史籍,我们去乌镇“随便走走”,恐怕河的记忆会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乌镇的河,不多也不少,东西对应,北三条南二条。太密太多也会影响情绪,意大利的威尼斯,整个儿浮在水面上,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太少,也就缺乏一种灵秀,缺乏一种湿润,让人有种枯涩的味道。所以,看来看去乌镇的河,养育了乌镇这样一个中国古镇,这恐怕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假如位于乌镇五百米的高空,俯瞰这个古镇,可以看到不成规则,然而纵横交叉的河流,整个儿像一个人的经络,环绕在乌镇内外,让人心旷神怡。沿街的河,沿河的街虽没有富丽堂皇,金碧辉煌,却富有神韵,风情万种!乌镇的河,处处显示一种文化一种情愫。那位让人永远景仰的文学巨匠,远离故土,奔波在尘土飞扬的大西北,却不禁神驰万里,午夜梦回橹声欸乃的故乡乌镇,这是何等的情怀!倘是清晨,河中水气氤氲,一轮朝阳朦胧水雾的遮挡下,轻轻地从河的东边升起,没有灼人的光芒,只有水样的宁静和灵秀。早起的人们在河边洗刷的场景,更是北方同胞所难以想象的现实,连城里见多识广的人也疑为仙境。众多河流,仿佛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小孩,而且也都有一个或雅或俗的名讳。镇中间的市河,大名为[车溪],史书上有“裂车溪”为东西,东为青镇,西为乌镇的说法。镇南有“金牛”、“白马”两条河,穿镇而过,向镇北澜溪塘、紫云塘、横泾塘流去其他的河港,也是百花齐放,浮澜桥港、虹桥港、百子桥港、白娘子港等,听起来让人悦耳。在这些很有古典色彩的河港里,小船悠悠,的笃的笃的竹篙在石帮的支撑声,吱呀吱呀的摇船声,及每个人的心里千言万语的感受,构成了一部水乡交响曲,它不仅回响在宇宙天地间,而且回响在每个游过乌镇的人心里。
坐在河边美人靠上,望着河里来来往往的船只及各式人等,仿佛是凝望人生往事,当年的河今日的水,要追寻当年的水犹如追当年的阳光一样困难。但翻开日月如梭的历史账册,让人吓了一跳!乌镇所在县市——桐乡这个地方,水乡古镇之间相距不过二十里,但都多河港——只不过多少而已。而且河港狭窄得令人不可思议,20世纪40年代后期,实测石门湾的市河只有3米宽,洲泉镇市河5米宽,灵安镇市河6米宽,崇福镇南市河6米宽,而东市区市河仅2米宽。而今日乌镇50多米宽的市河,在50多年前也是“阔不盈尺丈,河中只容一舟”。到1948年,乌镇市河在北花桥一段,宽度不到2米。所以当年遇到大旱时,连小孩也能一跃而过!想想这些历史情景,望着这碧波白练似的河港,一种沧桑感立刻浸淫全身。
河流的众多,使乌镇这个古镇多了一些韧性。千百年来,古镇在兵燹和天灾之下,几处毁了建,建了毁,始终绵延不绝。这种坚韧的古镇性格,我看相当部分是得益于水的韧性,这种性格同样也养育了勤劳而充满智慧的一代又一代的乌镇人。水文化使乌镇更秀美,这恐怕是到过乌镇的人都会有的一种文化体验吧。其实水不光对乌镇有这般厚爱,世界上所有名城名镇,都是这样。大到巴黎,因为城中有塞纳河而使巴黎更灵秀,上海也因有苏州河、黄浦江而傲视东方。而有水乡之称的江南,临水而居的习性造就了众多的水乡古镇。乌镇周边的南浔、石门、练市等,都是沿河而筑,由河支撑起一片天空。据载,乌镇有河道总长85.8公里,哪个镇有如此长如此多的河?一个镇的河道长度,乌镇是否能称全国之最?因此,望着那些纵横交叉默默无闻的河港,倾听着那些无言的诉说,让人心中涌起一种悠远的敬意,祈盼着古镇辉煌从河开始,流到永远。
桥,是乌镇的一大景观,是一种无言以说,却又不得不说的一种景观。因为桥在水乡的地位,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以为过,作为水乡来讲,基本上达到无桥不镇的程度,没有桥的镇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水乡古镇。水乡南浔,在清道光绪时有桥梁74座,同治时有107座桥,也是一个典型的水乡;而乌镇,河多,桥更多,据史籍记载,万历年间乌镇有77座桥,康熙年间有124座桥,乾隆时有116座桥,至今仍有39座桥!桥、不仅连接河两岸而且连接历史,连接未来,边接人心!一座桥就是一段历史,一座桥就是一个故事,也是这些桥,经历沧桑,支撑起一个古镇,滋润着这些古镇的文化。
桥是从古到今的通道,我没有考证,乌镇在历史上第一座桥在哪里,有没有名称?先人的智慧起先肯定锁定在生存和生活上,而精神上的需要肯定是后面的事,是先有了水,才会引水排水,然后有河,有河之后才有桥,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因此,当人站在桥上眺望现实,而从这现实里能看到历史的什么呢?阿弥陀佛,当阳光洒落在小桥上时,恐怕今人想到更多的是表面上的精美、古朴之类的文化,这些被称为文化的东西,给人带来某种虚荣的满足,带来某种愉悦和视觉快感!所以,现代世俗不必认真去考证乌镇历史第一座桥在哪里,而是只要看当下乌镇有那么多的新的、水泥构件的、石块垒砌的、沧桑的、水灵的桥,就足以让人们在乌镇盘恒和录访几天。当年林老板被逼债走投无路,冒雨踏上望仙桥时,本想从桥上纵身一跃,了此残生。然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声叫唤,把林老板想在桥上与死神亲密接触中拉开。而林板以破产的方式侵吞储户的积蓄,逼疯张寡妇后,自己却悄悄地从后门河埠下船,又从望仙桥下扬长而去,当然这是小说里的故事,但这是有关乌镇的小说,所以也很有参照价值。对桥墩的联想,简直就是生生死死和世态炎凉的联想。
乌镇的桥墩是很世俗的,光是从桥名看,可以说都很朴实。“卖鱼桥”就是集镇上一个鱼市场的所在地;“浮澜桥”就是因为捐资人是浮澜先生;而“宫桥”是因所处地方为“南宫”;“白娘子桥”就是建在白娘子港的缘故……但水乡的桥比竟不像一座山那样,千百年的站立着,往往不断地新建,也有不断的塌圮和废弃。所以,像修县志镇那样,桥也要不断面地机关报建和重修,因而更多地留有历史的印记,旧时代里诸如望佛桥,望仙桥等一看就知道不是50年代以来所造,而立新桥、红星桥、工农桥、新华桥、幸福桥等,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年代产物。但这些历史印记并不是褒贬时代的依据,桥的价值和内在智慧与历史印记无关,桥名和人名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
桥是一种文化,古往今来,人们都看重并精心呵护这桥文化。桥头倘有空地,必植杨柳桃树,春到江南时,桃红柳绿,小桥人家——将桥与家一样来并称如呵护,若是石桥,在造型上总要将造桥人的审美理想在桥的形状上体现出来。或置雕刻精美的石狮,或刻一棋盘供过桥人小憩,把桥装点成一种艺术,一种和精神、生活有关的艺术,成为人生间心灵沟通的一种桥梁。但作为置放在河上的石桥,又具有它的公共性,因而桥文化在公众视野里又成了公益文化。乌镇石桥上众多桥联既是一咱当地文人智慧的比拼,又是当地文人的素有桥里桥著称的通济桥面,面南的上下联是“寒树烟中尽乌戌六朝旧地,夕阳帆外是吴兴几点远山”,面北的上下联是“通门开数万家西环浙水,题桥人至三午里北望燕京”。一座桥,两副对联,写尽历史和地理,显示大沧桑和大手笔。浮澜桥墩有一展身手,如乌镇的翠波桥上有“一渠翠染诗人袖,终古波清客子心。浦上花香追屣去,寺前塔影送船来”。再如乌镇荐馨桥的桥联为“水隔一溪依依人影,塘开三里济济行踪”,“碧水半湾流野渡,翠波一曲抱祠堂”,都是在叙说桥的地理特征时不忘发一点诗性而凑上一联,变成犹抱琵琶半遮脸,中国的文人大都逃不出这个逻辑怪圈。
乌镇河多桥多已毋庸叙说,但乌镇西栅的通济桥、仁济桥却不能不说。这两座拱形石桥,年代久远,直角相交形成的桥里桥的视觉交果,很有现代风采。两座石桥的始建年代已失考,甚至边这种“桥里桥”的视觉交果发现于那一年,似乎也无从知晓。但这种“发现”,给水乡古镇平添了一道风景,使乌镇西栅的审美价值,人文和历史价值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傍晚时分,西栅外宽阔的河面、夕阳、碧波、白帆,宁静而富有诗意。可惜,这样的画面,只能让人们自己去想象了,而实实在在的两座石桥,经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仍相依相伴,忠贞不渝,尽管它们连手都没有碰过一碰!在人类看来它们仍相拥在一起,非常幸福!世界上有不少事,看过去是一回事,实际又是另外一回事,就这么有趣。
人类生息繁衍最紧密的,恐怕就是房子了,白天上班做工在房子里,晚上休息,也在房子里。因此,房子在人的生命历程里有着密不可分的作用。房子也是人类功名利禄的体现,正因为如此世俗如此精神,房子便成了世人的生活与艺术的基本载体。在传统意义上看,农村与城市城镇的主要区别首先也是在房子上。农民对房子地需求没有城镇上的人那么讲究,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田野里劳作,不需要一个雕栋画梁深院大宅来调节休整,一天劳累之后有一个让人休息的地方就心满意足。即使在雕栋画梁的屋子里休息,也早已疲惫得无心欣赏、无力欣赏,况且在自然经济时代,瞎灯黑火的晚上!因此,农村的房子几千年来发展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城镇。而城镇却不一样,当了官的人衣锦还乡要有相般配的房子来充当门面,发了财的人也要用房子来显示自己的富有。所以久而久之,城镇上的房子越来越气派,越来越艺术。而到了近代,一个城镇的房子代表了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而房子的结构,外观的式样,则代表了一个地方的文化水准。
其实,房子本身是平淡无奇的,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场所,因为有了过多的人文因素才引起世人的好奇,也正因为有了人文因素才有了欣赏价值。否则,在人人都有房子住的时代,还老远赶来看什么房子?
乌镇应该说是中国发展较早的地方,它在环太湖经济圈内是较发达的一个地方。杭州到苏州,从水路走,乌镇正好处在中间,去上海,去嘉兴,去湖州,去苏州,在公路铁路还没有的时代里,乌镇这个地方应该是最方便的地方之一了。交通一方便,经济尤其是商业就繁荣起来,结果是有钱的人也就应运而生,市镇规模逐渐扩大,房子这个经济发展繁荣的标志性建筑也会逐年增多,成为富甲一方的一个巨镇。如果要客观的描述乌镇房子的发展历程,大体是上述情形。
如果要微观考察乌镇建筑,那每一所房子,尤其是那些有钱有文化的人造的房子,每扇门,每根梁,每垛墙,都有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喜剧,有些是悲剧,也有些是关于悲喜交集的。但每一座房子,在乌镇都是一种文化。表面看,马头墙、风火墙,水阁楼,高低不一,形成一片片很有层次,很有色彩的画面,倘配上金黄色的斜阳,这错落无致的画面,也真是美到极致。还有小河—房屋—街道—房屋的建筑格局,使这个古镇始终充满水灵的秀气。但这是乌镇寻常百姓的居所,而那些高屋大厅的建筑,算得上是乌镇这些豪宅与豪宅都是发了财的富商或当了大官发了财后造的。不过有趣的是,乌镇这些豪宅与北方赵家楼、王家楼的叫法不一样。似乎一律叫做“厅”,如乌镇有徐家厅、王家厅、张家厅、朱家厅、桂家厅、陈家厅、赵家厅、金家厅等。 这些宅第,都有一个和江南人性格相似的特点,即外面看不出其豪,而里面尽显其广。一般的“厅”其实是一个大到五开五进的大宅院,但在外面小街上看起来一点都不显眼。一个石库墙门,两扇木门,推门而进是一个不显眼的开井,而穿过天井,是第一进二楼厅,再往里走,什么回廊,长方天井,楼厅也越来越轩敞,亮堂,可以说气宇轩昂,十分气派!其附加在厅堂上,门窗上的雕刻也十分讲究,古代小说里的场景,古代戏文里的故事,吉祥如意的寓意,在月洞门和回廊栏板上,随处可见。它表明主人身份志趣和爱好,也表明主人财富和地位,这种不显山露水是乌镇宅第与其絮絮介绍,不如身入其中,细细品味和寻觅,或许站在冬暖夏凉的厅堂埯,想像着当年红顶商人们的车水马龙,奴婢成群;也可想象当年达官贵人得意或失意时在厅堂里的种种情形;也可想象下人们蹑手蹑脚进进出出递茶送水。上至老祖宗,下至小少爷,尽在这些厅屋里演绎着人间的悲喜剧。这些称为宅第的厅堂,对当时人来讲都是身外之物,面对后人来看,却是难得的文化遗存。精雕细刻的栋梁,细镂而神态毕显的砖雕,设计高超、想象丰富的布局,让后人自豪,让后人叹止,陡增文化含量。走在逼仄的过道和楼梯上,仰望着宽敞的厅堂和气势不凡的匾额,体味着当年主人的心态,就会哑然失笑。这种既藏富,又想标示又不敢标示的尴尬心理,变成一种物质文化,一种流传几百年又让人揣摹几百年的文化!
乌镇的过去,曾经辉煌过,也曾经破败过,世事兴衰更迭是一种社会发展规律。当今天从西栅后边走去就会看到不少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前的辉煌,不过这些辉煌都湮没在荒芜的杂草里,当年的今只剩下断墙残壁,当年的小树早已在厅堂的废墟上长成大树,越过山墙,刺向苍穹,似乎在鸣不平,也似乎在显示自己的生命在绚烂的春天里。
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曾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核心问题,说一千道一万,都是一个大写的人字。无论历史风物也好,无论地理环境也罢 ,一切都是人所创造,一切为人所创造。再精美的房子,是人所造,也是为人所造;再有文化的桥,再有情致的小河中,都是人所造,为人所造。所以,一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活动”,既有物质的理解,也有精神的含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国乌镇这个古镇最大的物点是有许多没有。比如湘西那种崇山峻岭让人产生陡峭的敬畏感,乌镇没有;比如云南那种古朴风情里的少数民族情调,乌镇也没有。其实,这种没有也是必然的,中国的古镇之所以形成跨世纪的焦点和热点,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各不相同。人有我无,我有人无,而不是人有我优,这与商品经济的竞争是两码事。古镇是历史遗存,古镇是上苍的恩赐,古镇是先人的智慧。乌镇身处杭嘉湖大平原,但也不是北方一马平川意义上的平原,一望无际的概念在乌镇只有登到20米高处才实现。乌镇的地形地貌也富有人工意味海拔落差六七米的地形,让人真正领悟到什么是田,什么是地。田是水田,少则几亩多则上百亩,连成一片,颇为壮观。地是旱地,瓜果蔬菜,桑麻之地,地因隆起,因而称地墩,乌镇古时有乌墩之称,也因期限地貌地形如此的缘故。田低地高的地貌和网状的河流情形,养育了乌镇的蚕桑文化和水稻文化,这两种类型的文化的特点是春耕秋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典型的自然农耕文化这种文化养成乌镇文化,这两种文化的特点是春耕秋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典型的自然农耕文化。这种文化养成乌镇文化的性格,即实实在在的,不虚美不浮夸,绝无不劳而获的非分之想。当然这种文化是自然养成和历史造成的,与新世纪倡导的市场经济相牴牾。市场经济指导下的大棚农业已不再四季分明,不再春种秋收,冬天里依然春光明媚,冰天雪地里依然百花灿烂,果蔬不再四季分明,不再已忘记于今天是何季节。所以,历史有时候让人聪明壑智,有时也会让人糊涂。而湖涂在现在看来,主要是就历史的缘故。人们的命运,市镇的命运,历史的命运,恐怕都在时代的变迁中沉浮。当年这水田何以会比地低?地又何以成地,都离不开为人所创造,都是人的需要,因而毋庸置疑,人才是历史的主角。
田、地、河构成乌镇四乡地形地貌地基本结构,这种结构给乌镇这个历史古镇带来什么呢?假如溯源的话,恐怕镇上许多东西都可从这种三维结构中寻到源头。因为有地有蚕桑种养殖的习惯和传统,才有乌镇香市的形成,才有乌镇蚕花纸的销路,才有乌镇丝绸乃至印花布的诞生以及由此而延伸的许许多多故事。蚕桑文化浓缩到乌镇这个集镇上,平添一种神秘的蚕文化气息,正因为四乡有丰沃的土地,种什么长什么,才有乌镇姑嫂饼,才有乌镇的三珍斋,才有乌镇丰富多彩的小吃和点心;正国为有四乡农民早起进城交易的习惯,才有乌镇早市,才有乌镇茶馆披着晨曦点着灯笑迎四乡茶客;正因为四乡河道密布,旧时农民把造房买田地买船当作人生奋头目标。在乌镇,船是比田地还标志富贵的运输工具,摇船进乌镇便成了一道风景,引申出许多可圈可点的辉煌;因为有船,乌镇水阁下的河埠就格外考究,使得廊棚下的美人靠的用处也就有了多重含义。不光看河看水,更主要的是要看船及船上的人;也因为船是主要运输载体,镇上文化人格外重视桥墩上的楹联,这种楹联不是写给走在桥上的人看的,而是写给在河里来来往往的船上的的人的,让船上的文化人去品评的,正像当今公路高速化后,市县地界上竖的欢迎标语牌一样是给汽车里的人看的。因此,镇上的文化渊源,与四乡农村是割不断的,割断这种渊源关系也就是割断了历史,所以走到乌镇尽头,不妨进入乡村寻觅,感觉的天地将是崭新的,尤其是镇郊那片油菜花金黄时节,几可让人陶醉。
换一种眼光看乌镇,无论是人文,无论是桥还是河,无论是民居或相宅侯第,都可以读出多重含义,都可以寻觅到文化的隽永和经典。徜徉可以慢慢看,慢慢品,疾步可以领略乌镇文化性格中的快节奏。水乡的灵秀和阳光的充足,蓝天白云下老屋被抹上一缕阳光,让人感到历史的生命在复活。静物在运动,动物却凝固在历史的记录里,让人回味无究。无声的喧闹,让乌镇风情在大俗里得到升华。乌镇的香市古已有之,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档次不高却非常热闹,各不相同的心情汇成一个祈盼国泰民安的共同心愿,然而换来的是连年兵燹和天灾,失望了的百姓渐渐失去热情。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香市的热情为其他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所代替,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乃至当地年轻人记不起来香市为何物。而新世纪重新兴起的水乡香市,已不再是本来意义,化妆表演突出的是旅游风情,今人尽可一显身手或一笑了之。蚕花祈求也是表面文章,新世纪中国农民的观念也在与时俱进。
乌镇的民居或达官贵人的旧宅,整体看是一种和谐,马头墙、风火墙成为乌镇新世纪的一个标志,这种标志的丰富内涵凸显了平民化的文化特征。倘站在一个有意味的角度,审视并记录乌镇民居美的内涵,会有惊喜的发现,马头墙、风火墙竟和一般民居连在一起。并没有习惯想像中的贫富,高贵低贱者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而是紧紧地相依相偎,但是这是一般的审视和偶尔一瞥的心灵感应,仿佛丰富多彩的世界竟是这般美好。如果我们细细解读,贫富贵贱的区别依然那么寸土不让,豪宅大厅里的雕栋,全是有寓意的典故,那怕一块瓦当也是极具文化价值,类似上海石库门式的古镇墙门,门楣上的匾额,成为今天人们唯一的历史记忆。仰望着这苍劲有力的字体时,遥想当年风光,那也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平等和谐的。风火墙与马头墙壁还是有区别的,这是身份和地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而寻常人家的临街小楼,矮窗及窗口放的不是名贵花卉、而是一盆葱。一级台阶之上便是由森板拼成的[排门],不作店铺时,便由单扇小门任人进出,所以表面看来的“和谐”,区别还不是小截。不过在今天的百姓视野时,一切都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今天一切都也将成为历史,任后人评说,正像过去千百年的历史任今人评说而先人无力左右一样。好在历史是写在人们的记忆里,并且许多历史以文化的形态流传下来,好让人评说时有个参照。
说起参照,乌镇文化的视角,相对于都市文化,皇家文化而言,应该是平民化的。这种平民化主要在风格上给人印象强烈,小河边廊棚里,美人靠一开始就主人劳累后小憩,青石板小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中,有钱有权的人走在中间也成了普通行人,“回避”,“肃静”在乌镇历史上恐怕只有城隍庙出会时,才派用场。因此用再现情景的手法,回溯到乌镇历史场景时,应换一种眼光来审视,把它当作文化,这样也许更接近历史,其实,皇家文化的大气及君临天下的魄力,是一咱让人回肠荡气,让人感到宽阔无垠的博大美。而小镇,尤其是乌镇这样的千年古镇,则让人感到灵秀,感到精深。无论说历史,说人文,说建筑,说小桥流水,说园林,有一种说不完说不尽的精深感,品味起来,意味深长。
无论是落日还是晨曦,无论是朗日当空还中细雨霏霏,无论是白雪皑皑,还是阳春三月,既使不换一种眼光,乌镇也是非常耐看的一个地方。看到的是一种经典的江南古镇,看到的是一种种水灵灵的精美,看到的是一种妩媚。而假如换一种眼光走进乌镇文化性格,还能聆听到千年古镇的千年故事。一双眼睛就是一个镜头,镜头背后是一咱思考,无论是哲学的,还是文化的,是另类的,还是常规的,对中国乌镇的解读、理解、认识,公元一千年之后仍将延续着。